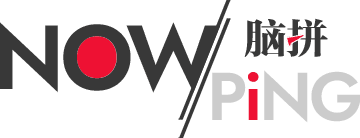郑永年:应付存在危机的三个“解放”与三个“回归”
文/郑永年
“存在危机”,或者说“存在主义危机”(existential crisis)本来属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术语,但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来直面我们当代人所面临的“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如果再借用另一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
存在主义源自人类的危机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经历了长达三十来的全球化,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几乎所有方面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毁灭也随之而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引下,国家会专注于收割由贸易和商业的自由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最终去除人类根深蒂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残留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概念),但是一战还是发生了。15亿人口被卷入这场战争,导致850万士兵和1300万平民死亡,21000万人受伤。更为深层次的变化发生在人类心灵深处。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类心理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即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早些时候所说的“上帝死了”。
尽管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人类越来越没有能力掌控一个被自己改变的世界,并且自己从富裕到死亡是一转眼的事情。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万物”的框架消逝,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作为个体的人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了。在个体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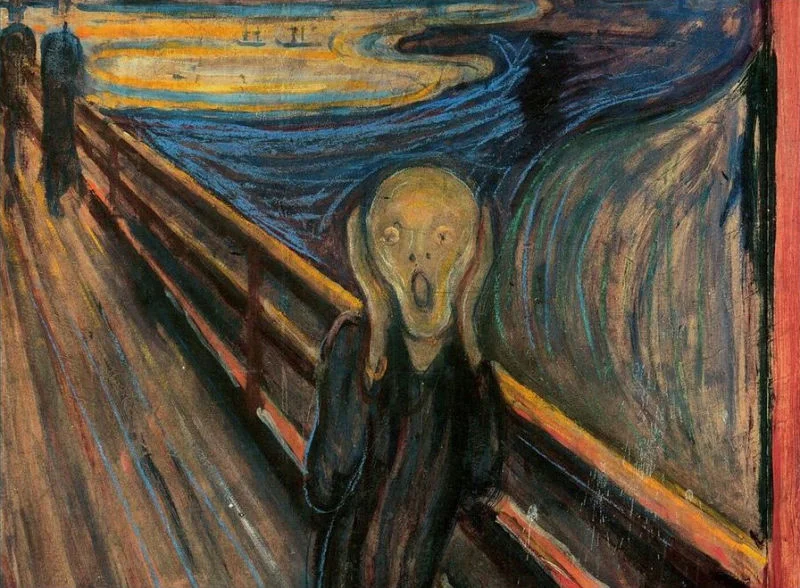
当代存在主义危机
存在主义产生于欧洲,流行于欧洲的知识界。它是欧洲富裕和死亡的产物。在亚洲知识界,存在主义流行于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之后,也和二战与其它形式的暴力和经济增长有关。当人们意识到人类刻意追求的富裕最终导致了毁灭(暴力与战争)的时候,他们觉得生命失去了任何的意义,空虚感油然而生。存在主义也因此被普遍批评为虚无主义。
存在主义危机是否能够解释当代的生存危机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毕竟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些方面,这两个时代是具有可比性的。
今天,主要国家内部都面临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收入不公和社会贫富分化等现象,在国际面则面临包括安全、经济和文明在内的全方位竞争。在另外一些方面,现在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而且并非处于同一等级或具有相同性质。存在主义危机主要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空虚”,因此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但现代人不仅面临着这个层面的“空虚”,更是面临着真实的威胁,不仅仅是战争的威胁,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威胁。尽管人类在以最大的努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但很多人还在假装这一技术不会替代和取代人类。尽管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类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变得越来越内卷。尽管人类物质现代化层面的成就前所未有,但人类找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寄托。概括而言,人类的确用自己的能力征服了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并朝着一个人类所不知道的方向运行,人类本身则被自己所征服的世界困住。
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个体层面的还是集体层面的,甚至是国际层面的,都是这些深刻矛盾的反映。焦虑、乏力、忧郁、啃老、无能、空虚、佛系、躺平、暴躁、自残、表现欲等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体现在集体层面,并且这些现象具有全球普遍性,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抑郁症是一种比许多人想像的还要更为普遍的精神疾患,其中,东南亚地区的抑郁症案例占比最高。
危机是实在的。因此,问题是如何从存在危机中解放出来。用中国人的语言来说,所谓的“解放”就是要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要回答为什么物质文明变得如此发达了,但精神文明反而出现那么大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从影响人精神层面的因素出发来寻找问题,进一步在此基础之上寻找问题的解决。
尽管一个社会的文化可以体现为物质领域的,也可以是精神领域的,但因为人是文化的最终载体,或者说,人是文化,文化最终必须是精神的。只有人是有精神的,离开了人,文化并无意义。因此,人们应当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人是如何塑造自己或者被塑造的?
三个“解放”:打破认知牢笼
人是根据自己的认知体验世界的,不同的认知导向不同的体验。因此,理解当代人的问题就需要理解人所接受的教育、所交往的对象和所使用的交往工具。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但要逃离或者脱离认知困境,有几个方面的解放问题可能是必须回答的。
1.如何从现代“心灵鸡汤”中获得解放?
“心灵鸡汤”是现代教育系统的主要产品。几乎从幼儿园到大学,一路走来,学生获得最多的差不多就是心灵鸡汤了。心灵鸡汤是全方位的,有道德的、伦理的、形而上神学的、形而下世俗意识形态的、软力量式的。很多被称之为“教育工作者”群体的人们扮演着“世俗牧师”的角色。任何社会都需要心灵鸡汤,因为其主要功用便是驱使人去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这个现实社会。它是任何社会的生存和稳定所需要的。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概括了心灵鸡汤的这一功能。
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心灵鸡汤可以有一点,或者必须有一点,但如果被过度地灌输,那么就会物极必反,与人性相悖。经验地看,越来越多的个体出自原始本能的“野心”已经消失贻尽,被文明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表现为对环境的绝对顺从,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但实际上,这种文明是虚伪的,因为人的本能被心灵鸡汤驱逐到心理的最深层次。潜伏在最深层次的人的本性不时通过各种形式表述出来,尤其是暴力形式,最极端的便是对自己的暴力或者对他人的暴力。因此,现代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然,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即使是个体本身也不知道今天自己会如何行为,会发生自己不可测的行为。
2.如何从社交媒体解放出来?
社交媒体是当代人的主要交往对象。需要强调的是,社交媒体已经不再是人们所说的交往工具,而成为人们的交往对象。社交媒体的普及是当代技术进步的象征,但这一技术已经有效深度捆绑了个体的时间。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讨论所谓的“注意力”问题,因为现代人每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社交媒体上。不仅如此,一旦离开了社交媒体,个体就开始感觉心理的不适,甚至生理的不适。
社交媒体剥夺了个体“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间和权利。在社交媒体中,人是绝对孤独的。汉娜·阿伦特曾经论述个体是如何被“原子化”的(她那个时代的人),她把“原子化”的原因归诸于政治,认为是政治上的专制或者集权导致了个体的“原子化”。但现在看来,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可能的,即“民主”或者“极端的民主”也会同样导向个体的“原子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社交媒体是民主的有效工具;亦有很多人说,社交媒体本身就是“民主”。很显然,社交媒体是高度“分散”和“分权”的,人人都有话筒,人人都可以发言,并且从理论上说,人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的。但从本质上说,社交媒体并非人们所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尽管个体身处社交媒体庞大的“人群”之中,但这些个体毫无有机关联,是互为孤立的。
实际上,这种孤立较之阿伦特所说的“原子化”更甚。在阿伦特所说的环境中,个体依然有交往的愿望和冲动,只不过是环境不被许可这样做,但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自以为或者假装在交往,并且是自愿的。也就是说,这种社交媒体的假性交往完全替代了真实的交往,并且有效地扼杀了人的交往的意愿和能力。
尽管不自知,但当代年轻人是悲哀的。今天的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实践者热衷于所谓的“注意力经济”(the Economy of Attention),即通过社交媒体剥夺甚至掠夺个体的“注意力”,借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人性的提升和升华是需要刻意努力的。在以往,社会的精英群体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前述“教育工作者”群体)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角色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分类极其简单,即“文明的”和“野蛮的”。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即人人都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文明。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精英毫无保留地使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资源优势,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迎合人性恶劣面来获取经济利益,并且这种迎合似乎表现为人性的需要,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这方面,知识界和商界趋于合一,对社会个体的掠夺性和剥夺性越来越甚,也越来越有效。
“注意力经济”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一项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当社会信息不断丰富就会导致注意力资源短缺的思想。它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在农业社会中最为短缺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在工业社会中最为短缺的核心资源则是能源;信息社会最为短缺的核心资源就是是注意力。
3.如何从人工智能解放出来?
社会形态是人最大的环境。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塑造着不同的个体。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很多年来,人们不断在讨论人工智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但这种讨论已经不足以叙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人工智能社会了。
迄今,人们关切着人工智能的伦理、隐私和各种风险等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甚至取代人类更多的活动的现实性。这些当然是真实的。马斯克预测未来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远超人类,数量可能是人类的5倍,甚至10倍;AI驱动的经济规模将是当前的数千倍甚至数百万倍,推动文明迈向卡尔达肖夫II型(恒星能源级),人类智能占比可能降至1%以下。他警告数字超级智能可能很快会到来,并且将比人类更聪明。马斯克因此把AI称之为“千英尺高的海啸”。当这场“海啸”到来之时,人类也就终结了。
就此而言,今天人们对AI的一些研究会马上变得毫不相关和毫无用处。人们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本身如何在与人类本身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保持优势,依然有能力主导和控制人类自己的创造物,而避免被人工智能所创造?
这方面人类的未来是悲观的,因为人工智能“赋能”人类的功能远不如其“去能”的功能。对一些人来说,人工智能是“赋能”,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人工智能是“去能”;对一些领域来说,人工智能是“赋能”,但对更多的领域来说,人工智能是“去能”。尽管人工智能赋予人类海量的知识,但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的知识不仅没有使得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智慧,恰恰相反,它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残”。尽管人工智能的“海啸”正在到来,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证实人类的“智残”现象。很现实地说,如果“脑残”趋势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社会必然很快演变成“牧民社会”,即人类被AI所奴役。
三个“回归”:摆脱精神危机
在意识到了现代个体文化是如何塑造和被塑造之后,人们就要回答如何解放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
1.回归知识
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改革迫在眉睫。少点心灵鸡汤,多点真实的知识。形而上的知识有一点即可,大量的知识必须和社会的现实是相关的和契合的。个体所获得的知识规定了个体成长的方向、路径、工具和手段。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决定其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及其如何成为。教育的本质并非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赋能个体在接受现存知识的基础上去创造新知识或者其它东西。人的意义不在生存,而是在存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创造。教育系统如果不改革,不仅仅是自身的危机,更是为社会个体制造危机。
2.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就是回归真实。现代人在温室中长大,在圈养中长大,没有一点自然属性。从前人们痛恨“狼性”,那是因为不够文明;但如果现代个体一点点“狼性”都没有了,那么也就失去了最为原始的“生存意志”(如果借用哲学家尼采的话)。
在温室中,在“羊圈”中,人不是真实的自己,人们所拥有的“自己”都是被“异物”所定义的,人们的价值也是用“异物”所定义的。在当代,不同群体的个体不仅活在算法中,而且其价值被算法所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已经失去了自我评估的能力(就此而言,人们需要担心,人类社会是否在告别“存在主义”时代,因为存在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自我评估能力)。
数字平台的算法放大了“信息茧房”效应,越来越多的儿童早早接触数字平台上海量的信息。
3.回归群体
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人工智能,都不构成社会群体,因为如前所述,这些不仅具有极度个体化和原子化的性质,而且提供给人们的都是迎合“人性恶”的假性知识。因此,需要回到面对面的真实社群,课堂、工厂、村庄、社区等等。对在社交媒体生活已久的人们来说,“回到群体”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在一些社会,人们已经开始用强行的方法把个体从“社交媒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例如一些学校开始不准学生把手机带入课堂。但就人类整体而已,人们还看不到如何解决“促成更多的人回归群体”这个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既是真实的,也是迫在眉睫的。这种危机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因为人类的大多数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是精神上的。但正因为是精神上的,才是最具有本质性的问题。正是精神才定义了我们是人。
###
来源: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