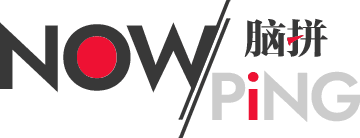欧阳哲生: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历史启示录
文/欧阳哲生
摘要:中西文化交流史作为一项专业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中西交流涉及两大关键概念:东西方、交通。中国作为“礼义之邦”自古重视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西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交流的方式和动力机制多种多样。文明互鉴是在文化交流中获取和实现的。中西交流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它蕴含丰富的文明互鉴内容,对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关系至密,文明互鉴是在文化交流中获取和实现的。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包含了物质、精神、制度多重层面。交流的方式和动力机制多种多样,经济、政治、宗教、科技甚至战争,都是交流的不同样态。中西交流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蕴含着丰富的文明互鉴的内容。中西交流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键环节,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项跨文化的交叉研究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族群在文化交流、互动中超越自身文化框架,主动认识、适应、吸收异文化,调整自身固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的动态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伴随中西交往而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项跨文化交际研究。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欧洲进入国人的视野。清朝前期官修《明史》,内中涉及介绍欧洲地理、历史者,即有《佛郎机传》《吕宋传》《和兰传》《意大里亚传》,记录的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可谓是较早记述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官修史籍。
鸦片战争以后,被战争惊醒的个别“先知先觉”士人从战争的硝烟中嗅到了不寻常的信息,他们开始了睁眼看世界。魏源撰写《海国图志》,其中卷三至卷七十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风俗、经济、政治和兵备,卷七十一至卷七十三介绍了外国教会、中西历法和纪年,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五介绍了先进的西方战舰、火器技术,并收录有《火轮船图说》《铸炮铁模图说》,卷九十六至卷一百介绍了有关地球和天文方面的知识。徐继畬著述《瀛环志略》,略述世界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其中零星涉及欧美各国的政情。这些介绍世界史地之作,显现了时人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初步了解,内中包含了不少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
不过,不管是《明史》的编撰者,还是徐继畬、魏源,他们都没有去过西方,也不懂西文,所写著作基本上都是依赖一些二手的材料编纂而成,尽管他们表现出探究世界的热情和冲动,甚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些闪耀着近代光辉的思想命题,但是他们的著述还是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史家对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曾加以考证,发现“邦国称名之误、方向错置之误、地势断续之误、部属遗漏之误、岛屿遗漏之误、岛屿错置之误、川名错置之误、东西互易之误、远近失考之误、大小失实之误”诸项讹误散布全书各处,这些错误的出现自然是作者的知识缺陷和视野局限所致。
真正现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1931年向达撰著《中西交通史》“小引”中称:“中西交通史在中国史学上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现在国内究心于此的很不乏人。”说的就是当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情形。陈垣(1880—1971)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对元史、宗教史颇有精深研究,留下了诸多著作,其中《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祆教入中国考》(1923)、《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合称“古教四考”,开辟了利用汉文文献研究基督教史的路径。他撰写的《浙西李之藻传》《休宁金声传》(1918)、《重刻铎书序》(1918)、《重刊灵言蠡勺序》(1919)、《基督教入华史》(1927)、《康乾间天主教之宗室》(1932)、《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1934)等一系列有关天主教入华史的著作,开中国学者研究明清天主教史之先河。陈垣还组织搜集天主教文献,发现并抄录了《名理探》《圣经直解》《利先生行迹》《天学举要》《铎书》《正教奉褒》《圣教史略》《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等史籍,开启了明清西学汉籍文献的整理。所有这些工作,显示了陈垣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张星烺(1889—1951)译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对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各国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作了编译汇集和系统梳理。该书虽为史料编译,但它构建的知识谱系和框架设计,奠定了中西交通史这门学科的基础,迄今仍是人们进入中西交通史领域必用的基础性参考书。
陈垣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26—1952),张星烺长期任教辅仁大学史学系并任该系主任(1927—1949),辅仁大学是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天主教大学,得中西交流之便利,因此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镇。
冯承钧(1887—1946)早年在比利时、法国留学时结识法国汉学大师沙畹,辛亥革命爆发后归国参政,1914年在教育部任职,1920年起在北大、北京高师兼职授课, 1926年第一本翻译出版的史地书籍是沙畹所著《中国之旅行家》。此后法国汉学著作经他手一本接一本地编译出版,如多桑著《多桑蒙古史》、布哇著《帖木儿帝国》、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记》、费琅著《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希勒格著《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沙畹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等,皆为中西交通史名著。当时国际学术界研究中西交通史以法国学者为翘楚,故国内学者得识法国汉学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全赖冯承钧之译介。冯氏还关注汉籍中西交通史之整理,为随同郑和出使的马欢、费信两人所写《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二书校注,为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清人谢清高《海录》、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等书校注,自著《中国南洋交通史》《景教碑考》《西力东渐史》等。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方面,冯氏可谓成绩卓著。1946年2月冯承钧逝世,向达作文悼念称:“近二三十年来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精深的研究,有系统地转法为汉,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近缘学,如西域、南海诸国古代的历史和地理,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启发者,还只有冯承钧先生!”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向达又为其作序,对冯氏在法国汉学、西域南海研究、印度佛学、元史、考古学诸方面的翻译成就,及有关南海史地研究、西域研究的成就作了系统总结。
向达(1900—1966)对敦煌学、中西交通史有精湛研究。1934—1938年他曾赴英、法、德等国访寻敦煌卷子、吐鲁番古文书,其主要译著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高昌考古记》等,著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敦煌变文集》《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郑和航海图》等。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向达勤奋耕耘,成绩卓著。沙知编《向达学记》(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收集相关回忆、纪念性文字,增进人们对向达生平与学术的了解。
方豪(1910—1980)早年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独立出版社1944年出版)、《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1949年去台湾后又著有《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两部名作,这两部书在20世纪80年代流入大陆,被多次翻印出版,是迄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通行的常备参考书。晚年方豪又将其相关论著汇集编辑《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卷,学生书局(台北)1969年出版]、《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学生书局(台北)1969年出版]。方豪去世后,其学生李东华将其遗著编为《方豪晚年论文辑》[辅仁大学出版社(台北)2011年出版],又撰著《一位自学史家的成长——方豪的生平与治学》[台大出版中心(台北)2017年出版]总结方氏一生治史成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方豪可谓海内外颇负盛名的大家。
此外,阎宗临(1904—1978)所著《杜赫德之研究》及有关中西交通史系列论文,张维华(1902—1987)所撰《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著,朱杰勤(1913—1990)所撰《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东南亚华侨史》及有关中外关系史论著,黄时鉴(1935—2013)所著《解释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东西交流史论稿》《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等,在学术界亦有一定影响,对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各有其独特的贡献。
新时期,这一学科继续稳固地发展,学界逐渐以“中西文化交流史”取代原有的“中西交通史”之名。这一名称更迭的背后,是研究范围和研究视野的相对扩展,这一时期值得提到的通论性代表著作有: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等。从中西交通史更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反映了学界同仁对这一领域的文化史归属的认同,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影响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东邻日本学者对东西交通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亦颇为重视,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专长东西交通史,著有《蒲寿庚之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和《东洋文明史论丛》等。佐伯好郎(1871—1965)以研究景教、中国基督教史著称,所撰《景教之研究》《中国基督教史》(5卷),迄今仍是这一领域规模较大的著作。后藤末雄以研究中法文化交流史见长,著有《中国思想西渐法兰西》《东西的文化交流》。矢泽利彦紧跟后藤末雄步伐,继续专攻法国汉学,独立翻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著有《西洋人所见中国皇帝》《西洋人所见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官僚》《西洋人所见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女性》《北京四天主堂故事》等。日本学者精于实证,重视宗教(佛教、景教、基督教)史研究,关注中国学界动态并存竞争意识,其成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相呼应,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最近四十年来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表现出三个重要趋向。
一是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新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涌现一批专家,都是以其所学外语专长进入这一领域,如耿昇的法国汉学译介和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金国平的澳门与中葡关系史研究、李明滨的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张铠的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研究等,他们分别利用自己擅长的外语,从区域国别角度介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2018年北京大学首创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被列为一级学科,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摆脱了以往那种泛泛之谈,进入了更专业、更细化的境地。
二是与国际汉学研究结合。随着中国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译介海外中国研究成果颇为重视,以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大量国外中国学研究著作得以译介出版。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刘梦溪主编《世界汉学》,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等集刊相继问世,引领了一股新的国际汉学研究热潮。国际汉学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国外汉学家及其著作、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等议题,这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本身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象,两者研究内容几乎相互叠合。
三是跨学科之间的相互合作。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项交叉性的、综合性的学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语言、文学、美术、音乐、科技、物质等诸多方面,人们可以从自己所处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相互之间合作交流,给这项研究提供了多学科的动力资源。新兴的全球史、海洋史、医疗史、科技史、环境史也包含了不少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甚至相互交错、叠加。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一项开放式、跨领域、多学科合作的研究,这是其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
从近三四十年来的新趋势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已突破了过去个人化小众作坊格局,形成了规模型“兵团作战”的研究阵容,如阎纯德主编“列国汉学史书系”,已由学苑出版社推出60余种,显示了这样的阵势。世界是在交流互动中发展,文明只有在互相交流中才能鉴别,这是由密切互动的世界形势决定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繁荣,正是当今世界学术界交流日益频繁的样态反映。
二、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样态
人类文明是在交流互动中向前发展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样态。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始于“地方”和“交通”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地方”即地域的方位名称,是地理学(geography)的研究对象。地理学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杂陈到科学的演进过程。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以其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人类面前,近代以后的地理学逐渐成为研究地球表层空间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
东西方概念在古代相对简单。上古时期的华夏大地,从地理形势上看是以东西相分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对此作了说明:“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种地理形势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最终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仍然是东西之间的战争。
华夏大地是如此,欧亚大陆也是如此。所谓中国人的西方与西方人的东方,在双方尚未产生实际交集时,只是一对邻近的区位概念。中国人最初的西方概念即所谓“西域”,不过是指今天的新疆、中亚、西亚一带。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到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的《新唐书》,诸史籍所载《西域传》反映了汉唐时期中国人的西方观念。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作为佛教圣地的天竺(印度)进入中原汉人的视野,“西天”作为天竺的别名,带有几分罗曼蒂克的异域想象。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正是民间长期流传的唐僧赴西天取经故事累积传递的结晶。
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东方(the Orient)概念,最早是指与其接近的古代埃及、巴比伦、土耳其等北非、西亚地区,近人称之为近东、中东。古代希腊人所称“光自东方来”(Ex Orient Lux)这句成语,有着某种憧憬的想象成分。同样,“东方”也是欧洲人想象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自古以来就寓意了罗曼蒂克的异国情调、遥远异域的美丽风景、古老童话般的历史记忆、艰难非凡的探险经历。正如东方学家萨义德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造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换言之,“东方”与“西方”是欧亚大陆两端相互对峙、互称对方而人为创设的一对名称。
如果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之所以出现“东方”“西方”这一对称概念,与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亚洲东边是太平洋,欧洲西边是大西洋,在遥远的上古、中古,这两大洋构成亚洲向东发展、欧洲向西发展的天然屏障。在陆地上旅行,亚洲人向西走,欧洲人向东走,虽然双方都要跋山涉水、翻越戈壁沙漠,但相对大洋航行,其风险和技术难度毕竟要小得多。所以欧亚大陆的东西走向,决定了双方的走向和彼此的互称。自古以来,东西方国家或民族向外拓展为何选择向东或向西的方向即基于这一缘由。
古代欧洲有过两次打通东西交通的努力:第一次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前324),第二次是十字军东征(1096—1291)。
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帝国,经过伊苏斯之战、高加米拉战役、吉达斯普河战役,相继征服了波斯、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最终在环地中海地区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东征最远到达印度河流域。随着亚历山大的东侵,希腊人移民迁入西亚,带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军事武器。与此同时,希腊也从东方汲取文化养分,与东方文化交流、融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后世的“希腊化东方”这一概念即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界定。
罗马天主教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1042—1099)发动争夺宗教圣地的战争,前后九次,时长近两百年,史称“十字军东征”。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激烈争战是东西文明的又一次大冲突和交融。经此战争,西方的物质贸易延伸到西亚、中亚,阿拉伯的数字、代数、航海术,中国的火药、罗盘针(也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入欧洲,对两大文明的交融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加深了两大宗教的敌意和隔阂。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人在成功击退了波斯帝国的进犯后,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东方’不同的身份。但直到很晚以后,即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东方’(Orient)才作为概念和术语,实际进入西方语言中。”
亚洲国家也有向西扩展的军事行动。13世纪崛起的蒙古民族以其强悍的军事实力发动了三次西征(1219—1223、1236—1242、1256—1260),先后建立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1219—1502)、察合台汗国(1222—1680)、窝阔台汗国(1251—1309)、伊利汗国(1256— 1335)四大汗国和蒙元大汗国(1271—1368),其势力范围远超此前的任何一个军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这些汗国连通欧亚大陆,为了强化被征服的广阔疆域内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必要联系,开辟海陆交通并建立通信驿站,从而使中国、中亚、西亚、北非、欧洲各地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更加紧密,为东西方交通、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新的便利。东西方在更广阔的视域中由相遇结成松散的整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尼哥罗·康蒂等横贯亚欧、亚非的大旅行家。现代研究蒙元史的学者将全球化时代追溯到蒙元帝国,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史应从这时开始书写。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西欧航海家迪亚士航行绕过南非好望角,达·伽马向东发现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及其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大航海时代来临了。这场地理大发现将分散的大陆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地球的完整面貌开始清晰呈现在人类眼前。西方航海家、传教士先后向东到达印度、爪哇、吕宋、中国、日本等地,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有了新的拓展。明代中国人也向西航行,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西亚乃至北非,郑和七下西洋走的就是这条航路,中国人遂有了模糊不精的“西洋”概念。从此,中西交通发生了从陆路向海路的飞跃。明末西方传教士介绍欧洲地理,艾儒略的《西方答问》中以“欧罗巴”对应“西方”这个概念。中国的“西方”与欧洲的“东方”真正有了彼此地理学上的对称和交集。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冷战的兴起,东西方这一概念又加入了意识形态内容,不仅是地理上的方位名称,还包含制度文化的元素。
与中西方关系和文化交流相关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交通。早期研究中西关系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都以中西交通史命名这一学科,显示“交通”与这一学科特有的关联意义。古代中文的“交通”一词源自《易经》的“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这里的“交通”意指天地之间的交流使得万物得以畅通无阻,上下一心则目标一致,所谓“阴阳相交,天地通泰”。可见,“交通”的原初古义蕴含丰富的自然、物质内容。《管子·度地》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 《庄子·田子方》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都是表示天地交、阴阳交,万物通达。先秦文献大体都是表达这一层含义。“交通”的第二层蕴含是道路、交流。随着中原与周边的联系、交流日益增多,交通有了交道、交流的含义,交通即为道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即含道路贯通、相互交往之意。“交通”的第三层意蕴是交流、通讯,这是与邮驿联系在一起的意涵。秦朝把“遽”“驲”“置”等词置于“邮”的名目之下,“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驿”字始见于《说文》小篆 ,本义指驿马,后引申出驿站、驿道、用驿马传递、两驿间距等义。交通与邮驿同义,交通包含了通信、通讯的内容。《后汉书·西域传》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这说明秦汉以后邮驿发达,交通有了新的提升。
文化交流与交通、邮驿在古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步入近代以来,人类为改善交通与通讯不懈探索。舰艇、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等新型交通工具接踵而至,海底电缆、电话、无线电报、光缆等新式通讯工具接续而来。这些都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因此日益频繁且便利。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产业发展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网络信息时代,文化交流不仅在同一平台进行,还可以隔空对话,在不同空间分享。计算机、互联网成为人类交流新平台,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成为地球与外星建立联结、传递信息的运载工具,古人的“嫦娥奔月”已不再是神话,当今世界的人类文化交流样态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三、中西文化交流是推动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崇奉儒学,儒家以礼乐原则处理中外交往以及中原汉土与周边的关系,强调“以礼待人”“以德服人”“怀柔远人”。《礼记·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居然强调修身养民、尊贤怀柔,这是儒家的“迂阔”之道。儒家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持守自己的这一信义原则。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因宋襄公过于讲究“仁义”,没有听从公子目夷的建议,结果兵败而受伤,这是信守所谓“仁义”的典型事例。《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德、义、礼、信、仁是儒家安邦经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对待邻邦远客奉行的准则。从文明进化的观点看,儒家持守的信念和理想的确表现了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华夏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的原理即奠基于此。
自古以来华夏就重视文化交流。《礼记·中庸》曰:“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在相互交往中,强调“厚往薄来”的原则,让对方获得益处,这是对待“诸侯”之道。秉持这一原则,历代王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款待四方来客,表现出大国的风范。
“华夷之辨”是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石,这一理论同样来源于儒家学说。《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华夏中心主义是以中原文明的相对优越性和生产力的发达为基础。陈焕章对此有精辟的解释:“春秋之义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及其反夷狄则夷狄之;中国而夷狄亦夷狄之,无通辞也,是故中国与夷狄,均无定名,亦无人种与地理之分,惟以礼义为标准。而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者,犹今日所谓文明野蛮也,此乃文化之符号,而非国界种界之区别也。”以礼义作为区分华夷之间的标准,显示出这一概念内含的文明意蕴。历代王朝更替、战乱纷争,儒家的这一观念始终没有被撼动,成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恒定准则。
明末清初中西初遇时,国人仍坚持以“华夷之辨”的理念处理中西关系,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抗拒与轻蔑。晚清以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传教士、外交使节、商人纷涌入华,中国固有的朝贡体制与西方的条约体制发生激烈冲突,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展开生死博弈,西方列强将所谓“万国公法”的国际秩序强加给清政府,“华夷之辨”的天下体系逐渐解体。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是在物质文化层面,通过经贸往来实现双边互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运往欧洲,销往海外;西方的玻璃、珐琅、钟表运到中国。所谓“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栗特商人、波斯商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中介商。南宋以后,由于战争的阻隔,通往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一条重要商道。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后,英国、荷兰、法国、瑞典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寻求向东方殖民拓展,与印度、东南亚、中国等东方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东西文明交流进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
宗教交流是古代中西文化互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宗教在上古至中世纪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轴心时代诞生的各大宗教,如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欧洲基督教等都具有神学性质。中国是世俗化国家,士大夫尊崇儒学,外来宗教要被士大夫阶层接纳,需要跨越较高的文化门槛。佛教入华是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汇,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降,士大夫甚至上层贵族、皇亲接受佛教,大大助长了佛教在朝野上下的影响,使其压倒中国本土的道教而成为第一大宗教。佛教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宋明理学即是儒、佛、道的综合。
天主教最早于元朝传入元大都,但信众较少,且主要集中在非汉族族裔。晚明时期,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内地,其影响范围拓展至东南沿海、江南、西南、京畿,甚至蒙古边塞。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获取中国社会的信任,他们采取“适应策略”传教,辅以承担其他方面文化交流的功能,诸如科技、美术、音乐方面的交流,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一波高潮。由于天主教的渗入构成“异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开始实施限压政策,嘉庆以后更是厉行“禁教”,天主教在内地转入地下,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解禁重开教堂。近代以后,来华天主教和新教与西方殖民势力联系紧密,其影响力覆盖了中国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教会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应运而生,其势力不可小觑,教案因此迭连发生。最初的教案主要是基督教与儒教(学)之间的冲突,传教士与信众为一方,地方士绅和儒生为另一方,双方争斗不止。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盛,20世纪20年代非宗教运动兴起,反映了新型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势力渗透中国的忧惧与反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教会学校实施注册立案,加强管理,客观上促进了其本土化的过程。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中央集权制和层阶分明的文官制度为主要特点,对外实行朝贡体制,秉持“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在政治层面的中西交流颇为有限。在汉唐时期,为应对北方匈奴、突厥的骚扰,中央王朝与西域各部落或邻邦缔结联盟,或通过和亲的方式,组建军事、政治同盟,以制衡匈奴、突厥的野蛮入侵。清末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对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探索与效仿,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采用共和制的国家。从变法到革命,中国政制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自我更新。汉代以降,历朝坚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训,迄至19世纪末严复译述《天演论》,宣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敲响民族救亡的警钟,中国得以转轨走上政制改革的新途,告别两千多年的帝制,实现了政治文明现代化的伟大跨越。
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前述亚历山大东征、十字军东征和蒙古族西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唐军与阿拉伯军激战,双方战俘将各自文明的技艺带给对方。一说中国造纸术因此传入西亚,远播欧洲;阿拉伯人的工艺技术也传入中原。这场战争在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远超出了军事本身。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国人从战争的挫折中认识到英夷的“船坚炮利”,痛定思痛,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再遭重挫,清廷被迫开启洋务运动,师法西方工业、军事,中国由此开始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运动。战争带来的军事启蒙,是文化交流极具冲击力的特殊形式,近代尤其如此。通过战争,人们对交战双方的实力、科技、制度有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比较,并对自身的短板有了切肤之痛的认识。战争是塑造近代文明的重要力量,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多与近代中外战争的冲击有关。当今世界文明秩序,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席位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仍承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格局。
四、从中西文化交流借镜文明互鉴之道
文化必须交流,交流可以带来新的文化元素,互通有无,相互促进;交流可以产生新的文化刺激,相互对照,取镜对方;交流给人想象的灵感,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任何优秀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获得验证。如何交流又颇有讲究,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实际上也就是文明互鉴的历史。文明互鉴只有借鉴中西文化交流之历史教训,才可能获取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政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取径,也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尚书·君陈》:“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明人袁可立自题勉联:“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有容乃大”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原则,也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理论支撑。
“有容乃大”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对内来说,包括举贤纳谏、博采众议,容纳朝野各种力量、各种意见以及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原汉族与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融合的整体。对外来说,是对异域文化的吸收。盛唐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集多元文化于一身,长安即外来多种文化的集聚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古都长安、洛阳和元明清时期的北京都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外来文化通过旅行者、外交使节、商人、留学生和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元素。中华文明之所以沉沉一线发展至今,大放光芒,与包容、吸收、融合外来纷呈繁杂的多元文化有关。
其次,文化交流要想占据制高点,就要走出去、迎进来,掌握对话的主动权。一般来说,当国力强盛之时,外来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旅行者以各种名义纷涌而入,多为寻求利益而来;而当国力衰弱之时,本国人员须走出去,向先进国家寻求真理。文化交流循依的原则是取镜强者,学习先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原则适应于古往今来,不可移易。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已经衰微难振,又不肯学习先进,吸收世界上其他优秀文明,则无异于自取灭亡之道。
文化交流要有层次感,真正深度的文化交流都是在高层次展开。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多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彼时中国士大夫受限于认知视野和出行条件,罕见远涉重洋、探访西方。中西文化交流实际局限在天主教信众的小圈子里,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晚清以后,中国向欧美、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走出国门,中西文化交流突破宗教的局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科技、军事各个层面展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才逐渐扭转被动的局面,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再次,文化交流是在异质文化碰撞中发现对方的长处和优势,认识自己的短板和缺陷,最终实现取长补短。不交流容易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交流才会发现不足。但交流又面临选择和弃取的问题,囫囵吞枣,不加甄别,自然难以消化;而选择本身又与兴趣喜好、价值判断甚至国家利益分不开。个人在文化交流中可能凭一己之好定夺,士人群体则离不开文化背景,政权中枢会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向背来作出甄别。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复杂面相,多与个人境遇、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族自信心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愿意学习,也善于学习的民族,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中华文化茁壮成长、日益壮大。
文化交流是文明间各取所需,发现为我所无、为我可用的东西。外来文化元素要融入中国本土,就面临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国人对待外来的新生事物,都会从最初的惊奇羡慕,到主动引进,逐渐接受、消化,最后使其完成本土化这样一个过程。未经自我消化或一番改造,就加以抗拒或囫囵吞枣,都是对外来事物不敬,也难以做到为我所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些东西可能如夜空中的星星,稍纵即逝;有些东西则可能经过消化后,沉淀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大规模的交流有两次,第一次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第二次是欧洲基督教传入中国。
佛教自西汉末年输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历经千年的求法、译经、传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压倒本土宗教成为最大的教派,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佛教从一个外来宗教变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吸收、融入和本土化过程,其间还发生过几次争议颇大的佛儒冲突,但到宋明时期,理学融儒、道、佛于一身,佛教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合理地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入华肇始于元朝,明末清初形成规模性影响。但基督教入华过程始终伴随着紧张的冲突,早期来华传教士为消解这种紧张,在传教之外,还做一些传播西方科技、工艺、音乐、美术方面的工作,且试图与本土的士大夫和睦相处,采取耶儒结合的“适应策略”,以化解双方的紧张关系。但罗马教廷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固守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以及清朝在雍正、乾隆、嘉庆三帝期间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告一段落。
两次鸦片战争以降,基督教凭借西方列强扩张之势,辅以其创办的医院、学校、慈善机构之力,在晚清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本土的乡村士绅和儒生对之始终持有抗拒的立场,教案冲突不断。20世纪以后,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推行新式教育;1912年蔡元培主持制定《大学令》,确立现代大学体制。随着中国落实西方的学科体制,教育体制完全科学化,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拒斥宗教,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兴起,基督教的文化输入遂由盛转衰,不得不选择本土化的路线。基督教之所以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首先是神权与皇权(政权)互不相容。西方以罗马教廷为精神领袖,其权力凌驾于各国国王之上,而中国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各大宗教不得干涉朝廷事务,且接受政权的约制。其次是基督教所梦寐以求的“天国”与中国世俗社会的理想格格不入,西方的“神道”与中国的“人道”难以融合。最后是以中国儒生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对基督教传入的戒惧和群起抵抗,使得“教案”迭起,这一矛盾的激化有力地阻抗了基督教对华的渗透。当然,基督教的“背时”归根结底与其遭遇的时代语境分不开。近代以后,一方面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从物质文化到制度层面,再到深层的精神文化,都对中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大踏步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中国由此启动了现代化运动。这一过程迄今仍在持续。人类文化的总体大趋势是朝着工业化、科学化、世俗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的近代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在西方是如此,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主要是选择那些与现代化相匹配的要件,大多是近代以后产生的先进事物。引进西方文化只有在改造利用、实现本土化后,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这就不难理解经过中西交融、结合所产生的中国新文化自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这与民主、科学的发展分不开。基督教不能承载现代化的使命,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主流。
最后,交流不是交易,但交流包含交易的成分,所以交流也面临着成本计算,有时成本问题甚至占比还很大。不计成本的交流必然要付出代价,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不可持续,还会留下后遗症。以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来看,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规模巨大。比起欧洲的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早,排场和气势也非他们所可比肩,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毫无疑问,郑和下西洋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对明朝来说,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没有获得实际的利益回报,时人已有批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一书提及明宪宗时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的批评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对后世而言,动用如此庞大的舰队出海远洋,人们没有看到所期待的对疆域的拓展。相对来说,哥伦布船队四次航行前往美洲(1492、1493、1498、1502),发现美洲新大陆,其船队规模最大的是第二次,约1500人,其他三次都只有一二百人,相比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官校旗军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其规模要小得多,实际花费自然也要少得多,但其收获与对人类的长远影响大得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常为人们称道的一个成功案例,他不仅开创了大航海时代,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地理面貌。
另一个事例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访华。该使团在大沽口登陆后,沿途受到清廷的热情接待,在北京、热河等地的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清廷承担,每天花费接待费用约1500两银子之巨;离京南下时,官员的陪伴和各地的接待,其花销之大,难以计数。据陪伴使团的清廷官员王大人向英方透露:“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马戛尔尼私人总管巴罗根据这一数字计算,使团从1793年8月6日进入白河起,到12月19日到达广州止,清廷总计为使团支出达51.9万两,即17.3万英镑。而英国方面“出使这个国家的总开支,包括礼品,不超过8万镑,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四分之一”。双方开销相当悬殊。大概因为这次接待的前车之鉴,清廷以后对于接待这样庞大的外国使团访华就不再感兴趣。1805年俄罗斯派遣戈罗夫金使团欲前往北京,抵达边界城市库伦时即被清廷叫停。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永乐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在清朝乾隆年间,都是明、清两朝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家大业大,但都经不起这样规模宏大的外事活动的消耗,其他时候就可想而知了。文化交流必须是双向对流、互惠互利,而不是单方面付出,否则就难以为继。那种不计成本、只讲政治效益、玩弄金钱的外交交流不仅过时,而且无益。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的成本核算也成为必要的程序,只有维持收支平衡的交流才合乎交换原则。
当今的中国文化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开拓的新文化与外来文化多种成分的结合,从大、中、小学的教育建制,到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迪士尼游乐园、海洋公园等各种文化设施的建构,从人们日常阅读的书本,到老幼皆看的各种电视电影、微信、自媒体,它们都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开放是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标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已与中外文化、科技、教育交流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在不断吸收、消化、整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本体,也不断形塑自己的面貌。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要充满自信、面向世界,还要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和自主能力。只有不断与世界互动和交流,中国文化才会真正激发出新的活力。
结 语
我们现今处在全球化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在五六个世纪以前早已开启,历史学家将其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大航海时代,但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已不可分离。互联网将世界联成一片,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能瞬间成为家喻户晓、人所皆知的新闻。世界不再是神秘莫测的,文化交流以快捷、轻便、简单、适用的方式为世界各地人士所共享,文化交流以人们不可想象的速度和新的样态迅猛展开,这一切都是拜高科技发展的恩赐。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得更加自信,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面临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挑战,挑战即机遇。从中国传统文化到近代新文化,再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经过时代的冲刷和漫长的积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中,当今的中华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股巨流。鉴往知来,中华文化必将在未来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大放异彩!
###
- 注释略。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