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当世界不再保证意义,反讽成为继续生活的方式
文/胡泳
他们的脑腐
2024年,“brain rot”(脑腐)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年度词汇。这个词在西方Z世代(90年代末叶至2010年出生的人)与更年轻的Alpha世代(2010年后出生的人)中流行,用来形容一类“低质、重复、黏稠、让人上瘾但无益的数字内容”,从TikTok上的无厘头短视频,到Skibidi Toilet(马桶人)这样的“离谱动画”,再到层出不穷的网络迷因语言(67、unc、rizz、sigma、fanum tax等)。同时,它也指代因过度消费这类内容而导致的个体在精神或智力状态方面的退化,表现症状包括长时间盯视屏幕、远离移动设备时出现焦虑,以及对有价值活动的注意力减弱等。
脑腐本身不是新词,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brain rot”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54年的著作《瓦尔登湖》(Walden)。梭罗批评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提出对琐碎思想的沉迷会“削弱心智”,被视为脑腐概念现代意义的思想源头之一。而从文化的角度溯源,这一概念的思想基础也远早于网络时代:1800 年,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批评“狂热的小说”;20世纪,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与赫胥黎(Aldous Huxley)则担忧电影与电视的心智影响。可以说,“brain rot”延续了西方文化史中对“低俗文化”“感官过载”的长期批判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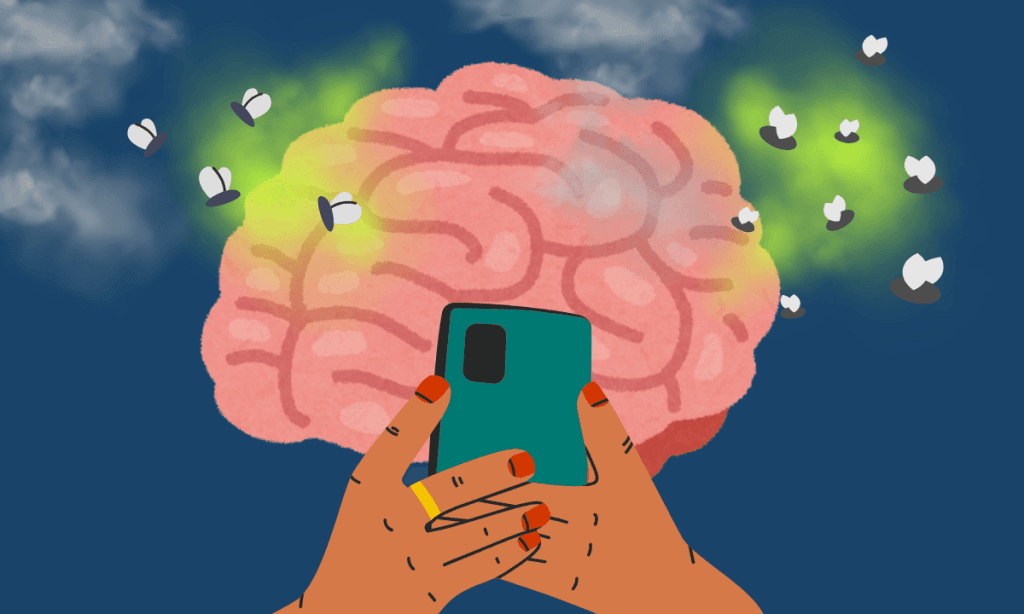
今天,从内容角度讲,脑腐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垃圾食品:情节极简、审美混乱、制作粗糙,却具有极高传播力。从行为角度讲,脑腐则与成瘾、分心、认知过载等紧密相连。内容也好,行为也好,这些断言都像是家长和老师辈对年轻人恶习的毫不容情的批评(虽然他们可能忘记了,他们的父母当年也曾贬低他们喜欢的东西)。不过让人意外的是,脑腐并非出自长辈的指责,反而是孩子们自己使用且乐在其中的词。它先在Z世代和Alpha世代的社交媒体用户中普及,然后反过来进入主流使用范畴。
《极度在线:互联网时代名声、影响力与权力的隐秘史》(Extremely Online: The Untold Story of Fame, Influence, and Power on the Internet)一书的作者泰勒·洛伦兹(Taylor Lorenz)表示,“brain rot”与“broken brain”(大脑坏掉了)基本同义。这两个网络词汇都可以用来形容那些被互联网低质内容严重扭曲的人,“他们已经丧失了在现实世界中正常运作的能力”。
若是这么说,称某人得了脑腐显然不是一种恭维。但有些人却在承认自己脑腐时,隐约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许多年轻人也似乎把脑腐当作一种荣誉勋章。他们会拿这件事开玩笑,对沉迷网络给自己身心造成的影响存在一定自知之明,但又不足以真正停下来。
脑腐一词的选择暗示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花了多少时间上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明白,他们看的许多东西并非最佳选择。然而奇特的是,即便他们正经历脑腐,也并没有将此当作远离网络的动力。
显然,脑腐在某种程度上对年轻人有用。问题在于,在哪些地方有用呢?
这首先是个语言问题。脑腐与年轻人讲话时频繁使用网络梗的倾向相关。造梗、玩梗,是一种语言游戏,本身就具备多重功能,如身份认同、自我保护、平台适配、情绪同步等;但最主要的,是对权威语言的去魅,通过拆解、挪用和戏仿,把宏大叙事拉回日常经验,重新夺回解释世界的权力。这是一种“弱者的语言政治”——不正面反抗,但持续消解。
青年一代不愿意融入上一代所确立的社会习惯,也不想沿用既有的语调与表达方式。相反,他们倾向于发明新的词汇、用法与语感,并通过这些语言创新建立起只在内部可被识别的信号体系,从而获得彼此的确认与归属感。某种意义上,这种语言更新的游戏几乎可以追溯到语言本身诞生之初:每一代青年,都会通过改写语言来标记自身的时代位置。
在美国,TikTok等平台上,Z世代的语言风格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一句话中若密集出现Gen Z词汇,甚至可能让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一时难以理解。这并非语言退化,而是代际区隔的体现——即划出“我们”和“他们”的边界。这种通过语言制造差异、建立身份共同体的冲动,正是青年文化亘古不变的特征。
这是为什么平台上会充斥大量只有刷过的人才懂的内部梗和小众引用。然而脑腐现象还不仅仅是梗化、迷因化使然。在表面的“恶搞”、“烂梗”之下,脑腐文化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深的时代现实——一种由焦虑、无力与高度媒介化世界共同塑造的青年生存方式。
年轻人明知脑腐是浪费时间,但并不会因此产生真正的恐惧或焦虑。更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以及生活中的东西,才是令他们感到担忧、困扰或不安的所在。社交媒体让他们接触到社会不公、气候危机、战争视频、仇恨言论。他们知道“信息越多,越无力”,了解“世界正在变坏”,但同时,又深感自己无法改变什么。
由此,脑腐文化与其说是无脑娱乐,不如说构成了一种应对机制。作为一个术语,“脑腐”绝不应被字面理解。那些将脑腐视为社会正面临的新兴心理健康危机的医学人士,尽管可能出于好意,但给出的定义并不准确。对许多人而言,沉溺于无休止的刷屏或长时间的游戏,更可能是在应对其他潜在心理或神经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麻木”,暂时缓解压力与不适,以及调节对现实的焦虑。
我们的抽象
与此同时,2024年,“抽象”成为中文互联网的年度关键词之一。与脑腐一样,抽象也富含梗化意义。可是,为何中国的互联网梗化被称为“抽象”?这源于一个自称“抽象工作室”的网络直播团体,出道时正值2015年前后网络直播初兴。工作室的创始人李赣,以及后来将其推向更大影响力的孙笑川,共同塑造并界定了所谓的“抽象”文化,使其渐渐从小众直播语境走向更广泛的互联网视野。
从语言层面上看,抽象这个词原本的内涵与脑腐具有相通之处,通过反讽、烂梗、错位模仿、刻意低质量表达,对严肃话语、主流价值予以解构。典型特征是:不是为了表达清晰的意义,而是为了破坏意义本身。这为后来的抽象美学奠定了基础。
同脑腐一样,抽象也并非简单的语言,而是一套社交密码,让同龄人通过共享的迷因确认“我们属于同一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脑腐与抽象都是新世代面对世界的共同语言。
发明新的语言,是为了建立新的共同体。共用脑腐或抽象的“烂梗”,是一种低风险的情绪分享方式,帮助青少年在失控的世界中建立稳定的归属感。抽象文化依赖大量链条化梗、圈层话语、语境知识、二级乃至三级翻译,造就一种“奇异的内容生态”,不过,从青年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了某种青年亚文化的新变体。
在研究者眼里,青年亚文化一向被视为一种“意义斗争的场域”,通过语言、风格、表演方式等,创造出与主流文化不一样的差异化标识。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抽象文化要进行再编码,形式包括:将严肃文本转化为抽象梗;对主流偶像、主流叙事进行荒诞戏仿;对社会性焦虑进行“抽象化转译”(例如把痛感弱化为笑点);利用二创、滤镜、配音形成反规范叙述。这些都体现了青年亚文化典型的“通过风格抵抗”,只是今天的媒介换成了平台化环境中的视频、弹幕与图文笔记。
早期抽象活动的核心平台是快手、B站的鬼畜与整活区以及贴吧后期的分化社区。这些平台上的抽象内容特征明显,如情绪过度或情绪失真,表达逻辑崩坏,语言碎片化与重复化给人以胡言乱语感,以及对“失败”“尴尬”“低能”予以主动展示等。2020年后,此类抽象借助短视频平台和算法机制迅速扩散,最终从一种边缘亚文化转变为平台化、日常化的通用表达语法。
在近期(2024-2025),“抽象”跃升为现象级词汇 ,部分原因正在于它已然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网络语言模式。现在,抽象已渐失当初的解构内涵,仅仅用来表达网上的一切距常规审美比较遥远、让人摸不着头脑又好笑的东西。
“抽象”一词东山再起所映照的,其实是互联网文化繁荣的消退,以及数字环境的结构性困境。当下的互联网已难以生成能够被广泛共享、反复言说的具象话语。无论任何“梗”,都会随生随散,既难以存留,也无法形成稳定而普遍的情感共鸣。在具象话语不断塌缩的语境中,大众情绪的表达失去了共同的锚点,互联网文化原本赖以成立的公共性随之瓦解。生活于网络之中的人们,最终所能勉强达成一致的,只剩下一种高度去内容化的“抽象”。
由此看来,“抽象”再度位居年轻人网络表达的核心 ,真正揭示的并非某种文化形态的回潮或复兴,而是当下互联网文化内容与情绪话语双重匮乏的现实症候。该症候所指向的,是一个让年轻人持续焦虑、疲惫、被动、过度曝光的世界。
在经典文化研究中,亚文化常被理解为对主流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抵抗。但在数字时代,抽象文化所面对的“主流”不再是父权体制、学校制度或大众媒体,而是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结构。此时的青年也不再通过反权威来表现差异,而是通过反常规表达在平台环境中获得可见性与情绪出口。
这样看来,今日的抽象,连亚文化都算不上,其核心也和抵抗无关,而是规避与适应。如果说此间还有某些抵抗的意味在,那也不在内容,而在表达方式。
这一代人的反讽性生存
他们的脑腐与我们的抽象,都具有共通的反讽结构:词语和行为本身毫无意义,却承担社群内部的意义制造功能。两者都通过共同理解的荒诞语言构建情感连接,依靠“符号的故意违和”建立玩笑和幽默机制,并藉由超现实表达无法言说的焦虑与无力感。
另一方面,脑腐与抽象,借用文化人类学家 Mimi Ito提出的概念,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参与类型”(genre of 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人们参与媒介、技术与文化实践的不同方式和层级,尤其强调参与并非单一形态,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兴趣结构与学习路径之中。当我们观照全球互联网青年文化的时候,我们并非仅仅关注内容的类型,而是更多关注参与方式的类型。后一种关注也就是要弄清,人们如何进入一个媒介环境,与谁一起参与,投入程度怎样,以及这种参与又如何同身份、学习和社会关系相连。
在像 TikTok、B站、快手、小红书这样的数字平台上,内容类型千差万别,而其中一种参与方式,是主动去寻找脑腐或抽象内容,像“关闭大脑”般放空自己。根据我的观察,这类无需动脑的内容(特别是短视频,以及新兴的短剧)在更大的互联网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参与形式的角度看,这些作用涵盖了对短平快内容的自我贬损式评价,对平台推送机制的直觉应对,以及对沉浸式数字生活的半自觉反思。年轻人绝不愚蠢,然而我们也需明白,他们并没有在寻找“退出方式”,至少现在没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充斥着各种如塑料一般的数字内容、数据与媒介,廉价、可塑、泛滥、难降解,却又长期滞留并影响主体与环境。年轻人不得不和这些数字塑料一起生活,就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哪怕食物里有添加剂、水里有氟化物、空气中有颗粒物,人还是得吃、得喝、得呼吸。
《纽约客》评论脑腐现象时,承认下一代只能活在上一代提供的条件之上:“事实上,这是我们给他们的世界。一个艰难、刻薄又愚蠢的世界,由监控人与马桶人共同统治。一个每天都变得更热、更脏、更丑的世界。孩子们只能在周围的所有腐坏中,尽力搜集能为自己所用的东西。”
无论脑腐文化,还是抽象文化,代表的都是一种弱主体性:它不以改变现实为目标,但能让个体在无法改变的现实中继续维持日常生活。这种主体性的弱化并非纯然是青少年的问题,而是时代所致。如果说,此前几代人的文化是对“意义”的追寻,那么,这一代的文化更多是对“过载意义”的排泄与调节。
这一代正在经历一种反讽性的生存状态。并非年轻人不肯严肃对待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现实压力过于真实、系统性问题难以改变,个体才不得不以反讽、戏谑和自嘲的方式继续参与其中。反讽成为一种生存策略,而非审美选择。它允许个体在“仍然身处体系之内”的前提下,与体系保持心理距离,从而避免被彻底吞没。
反讽性生存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既不完全拒绝参与,也不再完全相信意义。年轻人仍然学习、工作、恋爱、创作,但同时,通过数个层面的抽象,他们不断拆解这些行为本应承载的宏大意涵。
在信息与符号层面,抽象表现为表情包、段子、梗图和二次元头像等形式,以轻量化的符号装置承载并传递情绪与态度;社会与政治意义上的抽象,以隐喻、幽默和代码化语言呈现复杂的社会或政治议题;情感与文化体验的抽象,将心理体验转译为可被快速识别、传播与消费的文本;而所有这些的背后,是让信息和表达脱离具体个体,沉淀为一种匿名、可复制的“公众心态”。如此,不仅可以简化理解复杂内容,更可以规避管理或社会压力。
这种状态并非全然的虚无主义,而是一种被迫的参与与清醒的共谋:知道叙事不可靠,却又不能退出游戏。当人既不能相信故事、又无法离开舞台,唯一可行的姿态,便是以游戏化、去意义化的方式继续留在场内。
因此,反讽性生存并非一代人的“态度问题”,而是一种跨越东西文化的时代症候:当世界不再保证意义,反讽成为继续生活的方式。
然而这反讽不是没有代价的。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所言,反讽是一副“存在主义的扑克脸”,一种“通过拒绝认真对待问题内容来阻断问题本身”的姿态。近年我越来越怀疑,我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反讽姿态——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究竟是否真的骗过了谁。
反讽的风险在于其长期悬置性。如果反讽仅停留在拆解、嘲讽与抽象化阶段,而不通向新的价值投入,它便会固化为一种情感麻木的常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青年文化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状态: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早识破叙事,却也比任何一代人更难重新建立真诚。须知,反讽并非终点,而是一道裂缝;问题不在于裂缝的存在,而在于裂缝之后,是否仍可能出现新的承诺形式。
在此,也许“马桶人”还有另一层更令人唏嘘的意义:它标示着当下人类心智所处的位置。此刻,只有两条路可走:向上,或者被冲进下水道的弯管之中。
###
来源:腾讯新闻大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