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臣》:“手术刀”和“透镜”下的盛世“切片”
文/于学周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卜键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0月第一版,75.00元
卜键先生新作《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实》,以“学术研究的副产品”自谦,却恰恰成就了其独特的价值——学者严谨的考据功底与生动的叙事笔触在此交融,将尘封的案卷转化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全书从乾隆四十六年起笔,层层剥开甘肃捐监冒赈案及相关联的陈辉祖盗赃案的真相。令人震撼的不仅是涉案金额之巨、牵涉官员之广,而是一种深植于王朝骨髓的、令人窒息的系统性困局,以及在这困局中人性如何被诱惑、扭曲、吞噬的悲剧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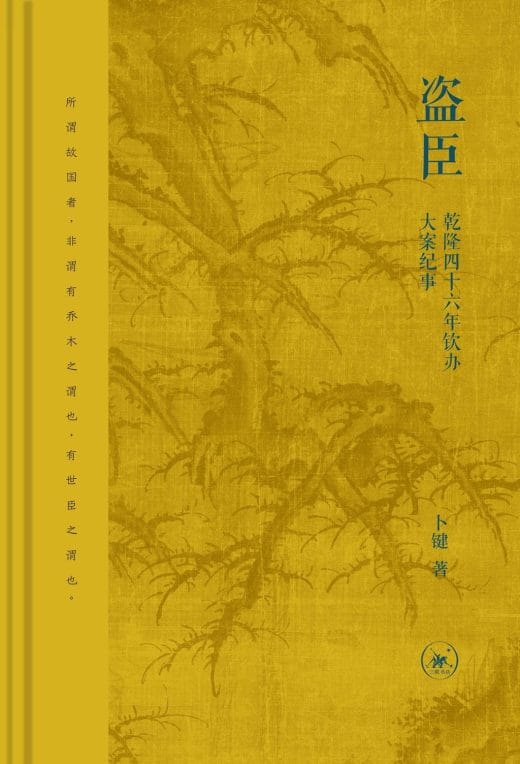
本书最为精妙的叙事张力,在于构建了一幅英明君王与无尽硕鼠的荒诞图景。乾隆皇帝,这位已御极四十六载、将屁股下的龙椅坐出了包浆,权力玩弄得“滴溜转”的七旬老人,试图通过提拔世仆世臣,来寄托“忠诚可遗传”的政治理想。尽管这只“老猫”目光如炬,可硕鼠却层出不穷,堪称辛辣的讽刺:他钦点的反贪干将(陈辉祖),转眼就成了新一轮的巨贪;他信赖的封疆大吏(勒尔谨、王亶望),构建了一个几乎囊括全省官员的贪腐同盟;他派出的钦差(袁守侗),也被精心布置的骗局轻易骗过。乾隆在明喻中的“愧疚”与愤懑是真实的,他对臣工要求不可谓不严,告诫叮咛不可谓不苦口婆心,惩治手腕也堪称凌厉果决,而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旧的硕鼠伏法,新的盗臣已然在暗处滋生。当然,卜键先生没有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帝王个人的失察或衰老,而是引导我们审视数千年帝制的文化土壤。
可将《盗臣》一书置于《万历十五年》所代表的历史写作谱系中考量。这类著作共享一种深刻的方法论:择取一个时空横截面,外科手术般精准切入,再辅以历史透镜对细节的放大与凝视,最终目的并非讲述孤立的故事,而是透过这一“切片”,诊断整个时代机体的结构性病灶。
乾隆四十六年,时值盛世巅峰,乾隆皇帝威权如日中天。然而,甘肃冒赈案,如一记惊雷,暴露了从地方到中央、从仓储到赈灾的整个行政系统的系统性溃烂。这并非个别人的堕落,而是由总督、布政使至州县官员百余人构成的、运转多年的“分利秩序”。紧接着,陈辉祖案则完成了更具毁灭性的证明:连帝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启动、用以清除病毒的“杀毒程序”(钦命审办贪腐的大臣),其核心组件自身也迅速被腐蚀。一年之内,两大案件环环相扣,以极高的戏剧性,让盛世华服之下最脓臭的疮痈无处遁形。
当“手术刀”剖开社会横断面,“透镜”则让我们看清细胞的病变。《盗臣》中充满具体的鲜活的细节:权力市场已经明码标价,关于王亶望的民谚:“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冰冷道出进入贪腐体系的准入价格。陈辉祖在抄家清单上将“金”改“银”、私藏古玩的举动,揭示了面对巨大诱惑,“黑眼珠见了黄澄澄金子”,人性的防线多么脆弱。
这些微观叙事,共同构成了一部帝国晚期官场的“潜规则运行图谱”与“人性异化记录”。它让我们看到,精心设计的制度(如捐监)如何在执行中被层层消解为寻租工具;道德说教,在利益的精密计算面前如何彻底失效;而身处其中的人,无论初衷如何,都极易被欲望裹挟、异化,从管理者沦为掘墓人,最终成为墓中人。

超越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对制度与人性进行叩问,正是此类历史写作的终极旨归。卜键先生并未停留在“明君震怒、贪官伏法”的戏剧性表面,而是引导读者进行一场深刻的追索:为何一位聪察睿智、勤政且掌控绝对权力的君主,所发起的雷霆万钧的反腐,依然陷入“前腐后继”“反腐者腐”的绝望循环? 答案直指传统帝制的核心困境:权力结构的单向性与绝对性——所有权力只对皇帝单向负责,缺乏横向、独立、有效的制衡与监督。监督者本身亦是最需被监督的对象,而靠皇帝一人的“锐利眼神”,并无法穿透层层叠叠的利益和人情网络。通过对一炮两响、一年双案的叙述,《盗臣》让我们目睹了乾隆盛世的自我耗散。作者的笔,既是史家的手术刀,冷静地解剖病体;也是哲人的透镜,聚焦于永恒的权力、人性与制度之谜。书中详述的陈辉祖案,也剖开了乾隆帝惩处贪腐的悖论与局限。陈辉祖的偷窃看似即兴,实则绝非偶然。它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时代,奉命去监督的人,往往成为最需要被监督的对象。
《盗臣》以“卿须怜我”作为尾声,如一枚冰冷的玉玦,为这部以制度剖析见长的著作,嵌入了最具象也最凄怆的人性注脚。王亶望的爱妾卿怜,在王被斩首后,很快被当朝权贵和珅收入府中。卿怜的遭遇,让本书在制度批判的冷峻之外,陡然增添了另一层关乎个体命运的、无声的沉重,提醒我们那被巨案吞噬的,除了巨额白银与数十官宦,还有无数被碾碎的、具体的人生。
###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