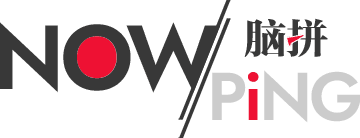米塞斯: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演进肯定沿着一条直线稳步前进
作者/(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翻译/王建民 冯克利 崔树义译
从分工演进的意义上说,社会进化是一种意志的现象:它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我们不考虑是否有正当理由把分工的每一次进步,从而把社会关系的每一次强化,都看作是上升到更高级的阶段;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种发展是不是一种必然现象。历史的内容就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吗?社会有可能静止不动或倒退吗?
我们必须先验地抵制任何这样的假设:大自然的“意图”或“隐蔽的计划”为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某种目标,康德就是这样想象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有此想法。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可以找到一条原理,证明连续不断的社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引起我们关注的第一条原理是自然选择原理。较发达的社会与不太发达的社会相比,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它们更有可能使其成员免遭不幸和贫困。它们也有更好的装备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侵害。千万不要受这种观察的误导:较为富有和文明的民族,常常在战争中被较不富有和文明的民族击溃。处在社会演进高级阶段的社会,总是至少有能力抵抗较不发达民族的优势。只有正在衰败的民族,正在从内部解体的文明,才会被正在崛起的民族击败。如果组织得较好的社会向较不发达民族的进攻认输,胜利者最终也会在文化上甘拜下风,接受被征服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甚至接受其语言和信仰。

组织良好的社会的优势,不仅在于它的物质福利,还在于从数量上说它的成员更多,从性质上说它的内部结构更牢固。这正是向更高级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社会范围更大,更多的人被纳入分工,人人更强烈地依赖于分工。较发达社会与较不发达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成员组成了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体,这排除了用暴力解决内部冲突的可能,并且对外形成了对抗敌人的严密防线。在较不发达社会里,社会纽带依然不牢固,每个成员之间存在着出于战争需要的联盟,而不是以共同劳动和经济合作为基础的真正团结。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相比,这种社会发生分歧更容易,也更迅速,因为军事联盟对其成员没有牢固而持久的控制力,从其本质上说,它仅仅是出于对短暂优势的期望而维持在一起的临时结合,一旦击败了敌人,开始争夺战利品,这种联盟就会土崩瓦解。在对抗较不发达社会时,较发达社会总会发现,它们的最大优势在于敌方的不团结。处于低级组织状态的民族只是暂时合作以图军事大业,内部不团结总是会很快使其目标分散。蒙古人在13世纪对中欧文明的袭击,或土耳其人为渗入西方做出的努力便是例证。用斯宾塞的话说,工业型社会对军事型社会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为军事目的而形成的联合,总是因为内部不团结而分崩离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条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范围的扩大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早就得到了证明。对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有机体来说,其范围之外的民族是否继续在低级社会演进水平上保持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存在,绝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对较发达的有机体来说,即使较不发达的有机体继续保持低水平在政治和军事上是无害的,即使占领其自然生产条件可能欠佳的领土没有什么直接好处,将较不发达的有机体纳入其经济和社会共同体也符合它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实行分工的社会里,扩大劳动者的范围永远是一种优势,因此一个效率较高的民族,也可以通过同一个效率较低的民族合作而得益。正是这一点,经常驱使社会高度发达的民族通过吞并那些迄今难以接近的领土,来扩大其经济活动的范围。位于非洲和亚洲的近东和远东落后地区的开放,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所以,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我们就看到一个全球社会的梦想正在实现。战争只是暂时打断了还是彻底摊毁了这一发展进程?可不可以设想这一发展进程可以停止,社会甚至可以倒退?除非同另一个问题即民族的消亡问题联系起来,否则这一问题无法获得解答。人们习惯于谈论正在衰老和消亡的民族、年轻的和古老的共同体。和所有的比较一样,这种比较是不全面的,而且我们一再得到忠告,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要抛弃比喻性的用语。这里所呈现出来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显然,我们切不可把它同另一个同样有难度的问题,即民族素质的变化问题混为一谈。1000或1500年以前,日耳曼人说的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语言,但是我们不应据此认为,日耳曼的中世纪文化已经“消亡”。相反,我们在日耳曼文化中看到了一条不曾中断的进化链条,从《救世主》(Heliand)和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姑且不提那些散轶的文学遗作)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确实知道,在数百年时间里已被日耳曼殖民主义者同化的波美拉尼亚人和普鲁士人已经灭绝了,但是我们很难认为他们作为民族变“老了”。若是把这种比喻贯彻到底,就不得不谈到那些天折的民族。我们不想讨论民族的转变,我们的问题与此有别。国家的衰落也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因为这种现象有时随民族的衰老而发生,有时则与它无关。波兰古代国家的覆灭同波兰文明或波兰民族的衰落没有任何关系,它没有阻挡住波兰社会的发展。

人口减少、福利缩减、城镇衰落,这实际上是发生在所有文化衰老事例中的事实。只要我们把民族的衰老设想为社会分工及社会的倒退,所有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就昭然若揭。例如古代世界的衰落就是一种社会倒退。罗马帝国的衰落,只是古代社会在达到一个高级分工阶段,然后又退回到一种几乎无货币经济的结果。城镇人口的流失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短缺和贫困现象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这种处于社会分工低级水平的经济秩序的较低生产力。技术渐渐丧失,工艺才能衰退,科学思想缓慢绝迹。用来描述这一过程最恰当的概念便是解体。古典文化的消亡,是因为古典社会发生了倒退。
民族的消亡是社会关系的倒退,是劳动分工的倒退。不管每个事例的原因是什么,实际招致衰落的一向是社会合作制度的终止。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度是个难解之谜,但是我们现在惊恐地看到,这个过程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之中,我们对它的理解更清楚了,虽然我们仍然无法认识到这种变化最深层、最终极的原因。
使社会得以形成、发展和维持的,是社会精神,即社会合作的精神。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社会便会再次四分五裂。民族的消亡是社会的倒退,即从劳动分工向自给自足的倒退。社会有机体分解为它由以开始的细胞。人依然存在,但社会消亡了。
没有证据表明社会演进肯定沿着一条直线稳步前进,社会停滞和社会倒退乃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世界史是已消亡的文明的墓场,在印度和东亚,我们都看到了处于停滞状态的文明的大型实例。
我们有一些文学和艺术小集团,对自己微不足道的作品夸大其词,同真正伟大艺术家的谦虚和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说,只要内心的文化得到强化,经济的进化是否继续无关紧要。但是,所有的内心的文化都要有实现它们的外在手段,而这些外在手段只有通过经济上的努力才能获得。当劳动生产力因社会合作的倒退而衰落时,内心的文化也会随之衰落。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以及劳动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常常要抵抗那些对文明抱有敌意的倾向和运动。它们会经常取得胜利,但是先后衰落了。它们受到解体的幽灵的摆布。通过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人们第一次知道了社会进化的规律,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文明和文化进步的基础。那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岁月,从未想象过的前景似乎正在打开大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由主义必须面对倾向于导致社会解体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对抗,尤其是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学说的对抗。民族主义理论自称有机论,社会主义学说自称社会理论,其实二者却发挥着反有机体和反社会的作用。
在对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制度的所有指责中,最愚蠢的说法是,它是一种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制度,它将社会机体原子化了。贸易并不像对地球上少数经济自给自足地区欣喜不已的浪漫派所断言的那样,起着解体的作用,而是起着团结的作用。最先形成社会联系的是劳动分工:它是纯粹而简单的社会要素。无论是谁,只要提倡民族和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就是企图使全球性社会解体;无论是谁,只要企图通过阶级战争摧毁民族内部的社会劳动分工,就是反社会的。
在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全球社会在过去200年中一直在慢慢形成。它的衰落将是迄今为止绝对举世无双的世界性灾难,各民族无一能够幸免。那么,由谁来重建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呢?
###
来源:《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王建民、冯克利、崔树义译;中国社科院出版;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