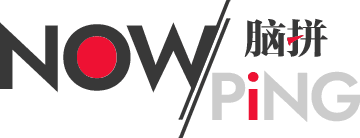周其仁:大变局的本底逻辑与未来机会
文/周其仁
题记: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在2025财新夏季峰会上的演讲,文字经作者修订,收入2025年新作《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并公开发表。
不管有无准备,我们都必须面对大变局。何谓大变局,是不是可以说,大变局就是全球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比较根本的是美国的变化,因为美国的变化对全球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中国走上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之路,离不开在冷战终结前后中美关系从对抗转趋缓和,中国抓住了当时全球变局带来的历史机遇。
1978年10月,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受命带队中国科协代表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达成关于派遣留学生的11项口头谅解。1978年年底,首批中国留美学生抵达美国。1979年1月,这份口头谅解协议在邓小平访美时正式签署。1979年7月,中美在北京达成双方互享贸易最惠国待遇协议,两国市场互相开放。虽然还需要年度审议,但不论经过多少风风雨雨,中美贸易互惠协议一直延续,直到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此后中国也正式加入世贸组织。1992年10月,华晨中国(CBA)在纽交所挂牌,发行500万普通股,每股招股价16美元,被超额认购85倍,募资7000多万美元,上市首日该股股价劲升25%。我翻看过那份招股书,封面上用小字披露风险,包括公司所在国度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私人财产可遭没收云云。
1988年我自己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受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邀请,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向留学生介绍国内改革发展情况。去了才知道美国大学已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留学生。次年机缘巧合,我得以到美国几所大学访学,然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书。当时我在国内的薪酬不可能负担得起到美国访学的费用,都靠争取美国大学给外国学者学生的奖学金。当时的个人观感是,“山姆大叔”富裕和发达不在话下,还很慷慨。当时接触到不少美国人,一般都没有那种看不起穷地方人的坏毛病。
事后看,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战后的巅峰时刻——自1945年以来美苏争霸的历史,以苏联垮台、美国完胜而“终结”。问题是,美国走向顶峰之后,除了回顾来路,自我陶醉一番,竟一路下坡。其中逻辑,顶峰终是分水岭,难有例外。特别是近些年,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人自己都觉得不认得美国了。2016年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看到几篇关于“锈带”的报道,找了个时间自驾去宾夕法尼亚,求一点现场感受。但见一家巨无霸钢铁公司,庞然大物般的机器设备无力拆除,全部锈死在那里。那可是曾给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供应过甲板、给旧金山金门大桥供应过桥梁的响当当的王牌公司啊!这类锈点还不是一个两个,要连成片,才形成“锈带”这么个经济地理学上的新概念。
流行之见是,美国人工贵,中国人工廉,一旦双向市场开放,海量中国商品卖到美国市场,海量美国投资则进入中国,这是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一个重要成因。一度我也相信这条解释,但反例也不是没有。那些比美国人均GDP和薪资高出一筹的地方,并没有因中国经济崛起而经济成锈。譬如瑞士,人均GDP高达10万美元,工资比美国还高,前几年我在日内瓦问过,瑞士失业率只有1%左右,周围几个发达欧洲国家的工人,每天跨境来瑞士上班。那又是个什么道理?全球化下廉价劳动力冲击发达经济体固然是一方面,但有没有应对冲击的恰当举措?更一般地看,所有先行工业都面临技术老化与后起之秀的挑战,缺乏有效应对,任谁也担保不了先行者能有长久繁荣。20世纪90年代,上海还有500家传统纺织厂,在浙江、广东等地的后发优势冲击下,上海纺织工人成批下岗,工厂成批重组。当时我参加地方再就业经验调查,还不是“无情调整,有情操作”,出台重组老上海纺织产业政策,重点培训中青年工人转岗再就业,同时发展上海新兴产业,熬过几年才化解难题。广东不算老工业基地,但开放后形成的工业能力,起步早,落伍也早,要靠一波又一波“腾笼”,才实现一波又一波“换鸟”。
以此看美国,问题并不是老工业项目遭遇新势力冲击,而是经济体系能不能应对“先发转落后”的挑战。不容易相信,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会匮乏到拿不出振兴国内产业那笔本金。美国的问题,是耗费过多资源维系全球霸权,在世界上摊子铺得太大,分明是个西半球国家,可东半球所有事务它都要插一手。“长臂管辖”固然过瘾,无奈越来越力不从心,结果自己国内的问题一拖再拖,积重难返。“锈带”不过冰山一角,后继的经济社会麻烦越来越离谱。

2022年疫情结束,我跟企业访学团去硅谷,落地旧金山,中午在联合广场(United Square)吃午餐,不敢相信这是2021年被评选为“世界最佳城市”的市中心:商店几乎全部关门,仅开着的几家中餐馆要上木板门窗私下招客;满街无家可归者,950美元以下的抢劫皆不入重罪,商场、酒店唯有关门大吉。还有2024年年底洛杉矶发生的两场山火,百十栋民宅遭烧毁,其中马里布那场山火,离我读书的UCLA不过10公里远,我的一位教授家住在那里,我发邮件问情况如何,回复是“家里烧得只剩一根烟囱”!不是说发达经济就不会遇到自然灾祸,但当着全球电视新闻眼,像帕利塞德(Palisades)这样的豪宅区可以连烧9天,“消防水龙头里就是没有一滴水”,任谁也无计可施,岂不是让人一窥其社会治理能力的本底颜色?
是的“,山姆大叔”越来越力不从心。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美国经济占到世界总量的50%,那是欧洲列强国力在世界大战中被消耗殆尽的结果。战后世界秩序不得不由美国主导。联合国总部在纽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在华盛顿,美元成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45年后,与美国争霸的苏联垮台,美国成为单一世界超级霸主,虽然那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最美丽,而只是一众对手相比而言变丑陋了。199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总量之比已降到不足30%,但它要管的世界事务却达到顶峰。此后看大势,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地在走下坡路。前文讲过的,顶峰恰成分水岭——对曾经的山巅灯塔之国,历史是不是照样很无情?
2024年美国经济占世界总量多少?26%而已。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美国占比更低。现在摆在特朗普总统面前两笔大账,一笔是1.2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逆差,另一笔是36万亿美元政府债务。行家早就阐释,美国贸易赤字与政府债务之间,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关联,解决起来牵一发动全身。除非改弦更张,否则美国经济无可持续。现实问题是,连自己国内事情都办不妥当,怎么还可以到处伸手管全世界,继续充当如在1945—1990年这一时期形成的全球霸主?且不论别人服不服,美国国内民众会不会答应?
从旁打量,“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含义,是“美国要把解决自家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这句口号也不是特朗普总统首创。自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开始,美国政治思潮里就埋下“孤立主义”传统倾向。2003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美国土地制度沿革,也知晓一些校园名人逸事。除了以利息理论名满天下的欧文·费雪教授,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有一位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此人是1940—1941年耶鲁大学在校本科生,带头掀起反对美国介入和干预欧洲战争的全美政治运动,创立“美国优先委员会”(The America First Committee)。虽说大国不免卷入世界事务,但“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却是常识级别的治国理念。毕竟,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世界总统,更不是人类总统。如若顾此失彼,发生重大偏差,美国政治逻辑终究要向传统回摆。
如此看天下大势,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无以为继。一方面是美国再也撑不住那么一种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是美国以外越来越多其他国家,越来越不接受美国霸权的继续。这个趋势洞如观火,无论理解上有多少不同,作为趋势性的现象,现实提供的证据几乎无日无之。
不大清楚的是,全球变局究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有多种理论推演,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那是凭大历史推断未来——当一个在位的老大,被后起之秀越追越近时,“战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位历史学家,研究古希腊两大城邦之间为什么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从中得出陷阱之说。当代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收集近代以来500年内出现过的16组类似状况,即一个在位强国遭后起之秀追赶,结果发现有12组发生了战争,但还有另外4组幸免。2017年艾利森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Trap?),时逢中美关系发生转折,一时洛阳纸贵。
2019年,我带了两个问题申请去哈佛大学访问,其中之一想当面听艾利森的阐释。不料讲座开篇,教授就说书名是出版商抓眼球之举。他本人研究的重点,是为什么那4组国家得以避免了战争,特别是关注中美两国各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有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艾利森教授也没有把握说,中美必无一战。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青少年时期天天听得“战争与革命”,轮到大学毕业,一路“和平与发展”走过来。现在可以说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不好说。举目四望,地球多地战祸继起,国家之间解决问题靠战争甚至靠核战相威胁。二十大报告里有一句新话,“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毕竟在世界竞技场上,自1890年后一直雄踞第一的美国,卫冕之战很吃力;1840年前的世界第一大国,近代落伍而在改革开放后越追越急。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14年就宣布新的世界冠军已经诞生。不过听我一句,与奥运会大相径庭,现实世界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竞赛,换冠军伴随换规则、换秩序,这才是现实的全球大变局。
202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请米尔斯海默来讲美国外交政策,事后看报道,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米尔斯海默讨论地缘冲突的出发点,是认定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并不存在最高权威可以仲裁国家间冲突;世界政治的本底逻辑,是“实力至上,大国为尊”。在此环境之中,大国争霸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实力分析出发,他认为美国不宜深陷欧洲与中东,应减少全球驻军,把重心放到东亚,因为中国崛起正形成一个可以挑战美国的“地区性霸权”。
米氏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新增第十章(以及与阎学通辩论的精彩记录),集中阐释上述分析与构想。此君叙事说理,直言不讳而理路清晰。读后有保留之处,是我觉得他的现实主义不够彻底,特别对美国战后至今国家状态的深刻变化,缺乏立足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我可能有点想当然,要是一代美国精英多到现场看看“锈带”,多听听美国乡下人的悲歌,那他们是不是更容易回答,美国是否需要更大幅度的战略收缩,以真正实现“美国优先”?
问题是,即便美国政治潮流向孤立主义回摆,做起来也不容易。独享世界霸权多少年,在种种惯性和既得利益支配之下,不是说收缩就收缩得了的。有一年在奥斯汀参观约翰逊总统图书馆,这位曾提出“伟大社会”、推动通过民权法案的美国第36任总统,展示给世人的竟是一副悲情形象:越战拖得他欲罢不能,时任国防部长不断报告,如不继续追加兵力,西方多米诺骨牌将全部倒下,苏联势力将覆盖全部东南亚。结果约翰逊一次又一次决定增兵,到他任期即将结束的1969年1月,派驻越南的美国大兵多达54.24万!越战惨烈史无前例,但尽管反战浪潮席卷全美,最后也拖上好几年,到1975年美国才以完败结局,撤出越战泥潭。
当下特朗普总统这波“美国优先”会不会利落一点?不好说。“美国优先”并非“美国唯一”(America Only),优先事项之外,其他事项也够他忙的。什么是美国的事,什么是与美国分不开的世界之事,界限划不得那么清楚。米尔斯海默也主张美国撤减全球驻军,不过他又画下一道线,绝不能因美国战略收缩,留出真空让其他“地区性霸权”冒头,将来反噬美国。米氏力推的“离岸平衡手”,想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倘若隔山打牛不见效,要不要开到“此岸”去呢?这样看,世界老格局翻篇与新格局成形,变数绝不会小。
唯可庆幸的是,处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无论走哪个方向,都离不开搞经济。战备和战争不但离不开经济支撑,还提供和平年代所没有的新刺激和新机会。更长远看,战乱和灾祸还可能推动经济重心转移,甚至生成新的经济繁荣。2024年财新新加坡论坛,我讲过公元10—14世纪的福建泉州——在北方游牧与农耕的地缘冲突中,避祸南下的北方移民创造出一个世界级的海洋贸易中心。类似的故事,还有20世纪上半叶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催生出美国经济的超级繁荣;1945年后美苏冷战,世界经济跑出的头马,既非美国,更非苏联,而是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后起之秀中国。全球大变局会终结这类故事吗?不会吧。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劳代尔曾经告诫,越是大时代,越要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里遭遇的变化与他们的行为应对。决定时代结局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物发现并抓住的新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