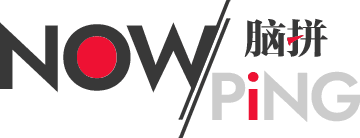周菲菲:“日本制造”的光与影
文/周菲菲
二〇〇八年,大量取景于北海道的电影《非诚勿扰》上映并备受瞩目。翌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个人游客发放旅游签证。二〇一〇年,我赴北海道大学留学,时值赴日自由行方兴未艾、“爆买”(“爆买”一词由日本媒体专门为形容中国游客大规模购物行为所创,并在二〇一五年入选流行语大赏)“日本制造”的热潮初现端倪。数码相机、电饭煲和手表一度被誉为“日本土特产三大神器”(〔日〕中藤玲:《廉价日本》,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留学期间,我曾就中国游客的北海道观光进行了参与观察和访谈调查。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的小田博志老师在指导该项目时,曾满脸疑惑地问我,他在德国留学时,日本产的钢笔、汽车等被当地人视为廉价的仿制商品,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喜欢?而我在札幌市商工会议所教授中文课时,一位八旬学员直言,在他小时候,日本制品不值一提,反而是中国产的热水瓶因其保温效果奇佳而被誉为“魔法瓶”(至今日语中保温瓶的正式名称仍为“魔法瓶”),因此看到诸多中国游客采购日本保温杯,他感到颇为不解。
时过境迁,“日本制造”的光环在屡屡爆出丑闻后逐渐褪去,但“日本制造”仍是解读战后日本自我认同、国际形象变迁及其国际关系构建原理的重要关键词。

一、边境意识”:战后“日本制造”的起源
“日本制造”在近代曾被贴上粗制滥造的标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日本产业整体遭到重创。为了出口创汇和挣脱经济困境,日本增加了生产日用消费品的比重,但在欧美市场仍未摆脱“便宜无好货”“垃圾产品制造者”的恶名。索尼(SONY)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回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海外销售史时提道:“日本制造的高端产品在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名气,不仅如此,日本制造还被贴上了品质低劣的标签。……最初阶段我们是想办法把‘日本制造’这几个字尽可能标记得小一些。”([日]吉见俊哉:《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SONY”这一国籍模糊的品牌名确立于一九五五年,融合了拉丁语中的“sonus”(声音)和当时流行的“sonny”boy”(小男孩)中的“sonny”。
为了扭转产品低劣的形象,日本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引进爱德华兹·戴明、约瑟夫·莫西·朱兰等质量管控方面的美国专家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工具。在他们的启发下,尼康公司推出了其开创性的、第一次结合光圈集成的曝光测光表并实现电机驱动的产品尼康”F。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年间,日本开展了被称为“昭和遣唐使”的大规模欧美视察团,令一万以上人次的企业管理者和工会人员亲眼看见并亲身学习欧美的管理方法。当时的日本制造业还实施了所谓“逆向工程”,即通过拆解和彻底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学习和模仿其设计。
正是在这一时期,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制造所研发了体积小、性能强、能耗低的袖珍收音机”TR55,这被誉为“日本制造”第一号。一九五七年,索尼公司推出的”TR60 收音机已是同类产品中最为微型的。他们在“努力实现零次品”的口号下将晶体管的良品率从5%提升到了90%以上。进入六十年代后,“日本制造”开始迎来黄金时代。
内田树认为,日本列岛的政治意识是从把自己作为“边民”的自我意识中衍生出来的,对中心文化产生既憧憬又自卑、既抗衡又认同的复杂心理,可归纳为“表面服从”, 内心不服”。正如日本在“二战”失败后把“昭和遣唐使”团派往美国,他们面对的中心文化这一“他者”,在近代以前是中国,“二战”以后则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日本人采取以“劣势”为契机、专心追求自身利益的生存战略”,结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日〕内田树”:《日本边境论》,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同样,日本美术也被称作“边境美术”(〔日〕辻惟雄:《装饰与游戏:解读日本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日本制造”亦然。可以说,在“二战”前积淀的技术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战后的“日本制造”顺应美国中心的世界秩序,安于承担在其中扮演经济发展中枢的角色,在全面模仿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前提下,生产出了各种比发明者制造的更为精巧的产品。
三菱综合研究所副所长牧野升提出了比“位居第二”更进一步的“1.5”技术论,相较于追求创新与首创,他更主张技术与产品的“生于欧美,长在日本”。松下电器的“位居第二”战略亦十分典型,即不侧重于研发新产品,在分析模仿竞争对手特定产品的基础上,通过极致的质量管理和价格控制而取胜。正如韩国学者李御宁所指出的,自明治维新至今,日本人一直以“追赶、超越”的精神对待西方文明,但这种文化的模式是”:如果没有谁为自己铺垫基础,自己的技巧就无法发挥(〔韩〕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山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降,“昭和遣唐使”团逐渐缩小规模或停派,“日本制造”摇身一变,成为超越者甚至引领者。到了八十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开始向日本公司学习。
二、“三神器”论”:“日本制造”的腾飞与神格化
如前所述,“日本制造”的战后腾飞扎根于与日本作为“边境”国家生存问题息息相关的技术信仰,因而也是日本这一民族国家的重要象征。正如加藤周一所言,代表日本思想的,是实践的伦理以及政治思想,或者说是与技术相结合的美学(〔日〕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虽然其目的是破解日本成功之谜以作为美国的对照,但其对日本的战后发展,尤其是支撑“日本制造”的管理模式的赞誉,令日本人陶醉于昔日老师的肯定。该著作的日译本从而成为日本出版史上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图书之一。
以高附加值技术为先导的权力话语塑造出了“日本制造”相关的各种成套的“三神器”(三種の神器)。日本神道所谓“天子三种灵宝”,即其所尊的“三神器”原为镜、剑、玉。伴随着战后工业的高速发展和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三神器”被用于指代日本特定年代的家庭与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电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日本家庭中开始普及的家电,成为日本人每天在家庭中体会战后日本技术主义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媒介(《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经济复苏初期,“三神器”指电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六十年代前期,彩电、空调和私家车成为新的“三神器”;到了二〇〇三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施政方针演说提及洗碗机、平板电视、照相手机是“新三神器”。
“三神器”原本就是把天皇统治日本列岛的权力加以正当化的物质文化象征,与日本国运相连。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〇年期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分割为“神武景气”(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岩户景气”(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伊弉诺景气”(一九六五至一九七〇)三个上升时期,这些名称都来源于日本神话,尤其是皇室谱系传说。相应的产品与管理模式神话也被归纳为“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部工会”的“三神器”论,强调把日本前近代的习俗惯例与西方科技相结合能够导向成功。尾高邦雄忧虑于这一神话的夸大和蔓延,指出其不仅不适合移植到美国,即便在本土,也已经呈现了滋生职工依赖心理、遏制自由创造精神、阻碍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导致人事停滞和职员工作乐趣与价值丧失等负面效果(〔日〕尾高邦雄:《日本的経営の神話と現実》,中央公論社,一九八四)。
当“边境人”摇身一变为主导者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括欧美人在内,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参照”[ 日”] 野口悠纪雄:《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机械工业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日本制造”的神格化集中体现了日本制造业民族主义的抬头。当时,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海外扩张已经引起了欧美的警惕乃至批判。在美国众议院议员于国会大厦门口锤碎东芝收音机时,彼得·戴尔的《日本式的独特神话》(一九八六)、卡瑞尔·范·沃尔夫伦《日本问题》系列论文(一九八六)、别府春海《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一九八七)等否定性看待包括“日本式管理”论在内的日本研究频频问世。面对国际上的负面评价,日本的官员们以及著名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被普遍敌对的受害者,他们倾向于无视所有不利的分析,并斥之为“排日风潮”(Japan-bashing)(〔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二〇年版)。当时日本的傲慢之处还在于,其忽略了自身成为战后第一个亚洲“经济奇迹”也是时势所致—战后几十年日本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同时,发家于模仿的“日本奇迹”的基本模式是可复制的,尤其在亚洲的近邻国家(John”Lie, Japan the sustainable society:The Artisanal Ethos, Ordinary Virtues,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Age of Limi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在发现亚洲邻国的模仿与创新足以超越日本时,日本经济学者篠原三代平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概念,称“回旋镖效应”,指日本援助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发展技术后,那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反过来利用学到的技术制造产品返销日本,对其国内产业造成打击的现象。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得到世界瞩目时,该词也用于形容中国生产的纺织品、家电、钢铁制品等压倒“日本制造”的情况。经济学者玉手义朗指出,“回旋镖效应”伤害了发达国家的自尊,时常演变为贸易摩擦。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施加高额关税或设置无意义的进口限制(非关税壁垒),减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容易引发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对立,阻碍了自由贸易。作为发达国家的“前辈”,不应去干涉“后辈”的工作,而应接住返回的回旋镖并掷回去,方能恢复尊严(玉手義朗:《ブーメラン効果”[boomerangeffect「] 後輩」の逆襲!》,情報·知識”amp; オピニオン imidas,二〇一二)。
三、“神性”消弭”:“日本制造”与“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制造”这一技术“神话”的瓦解,伴随着家电“三神器”一件件被物美价廉的中、韩产品替代,以及诸如三菱、日产、日立等制造业巨头的频繁丑闻。这一现象与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经历的经济衰退时期——即“失去的三十年”—”在时间上大致吻合。神户制钢的数据造假与奥林巴斯的财务造假都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自二〇二四年以来,日本制药行业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得“神药”的招牌蒙尘。继小林制药的功能性标示食品(日本保健功能食品的一种)红曲米膳食补充剂产品引发多起死亡事故之后,日本极东公司所生产的肠胃药“正露丸”被曝出成分不足,且该药品的实验数据被连续篡改了三十多年,同时存在采购原料时未进行质量检测等违法行为。
“日本制造”神话的消弭伴随着企业投资的下降、高速增长愿景的崩溃以及对市场信息和数字革命的迟钝。同时,支撑“日本制造”的管理神话也走向了末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不再得到保障,“企业内部工会”难以应对高失业率和非正规雇员的急剧增长等问题。事实上,日本式管理相关的“神话”源自美国人类学、管理学者阿贝格伦一九五八年的著作《日本式管理》,其是否真的捕捉到了日本企业管理的内在本质,本身就值得商榷。
政治学学者神岛二郎认为,战时日本军队的构建形态“单身者集团”是基于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日本战败后,这个体制并未解体,而是由企业(会社)接替国家与军队,继续以该体制吸收社会成员(神島二郎:《近代日本の精神構造》,岩波書店,一九六一)。韩东育指出,曾经的军事大国和当下的经济大国实际上是建立在相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的一体两面,因而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员工忠诚度的培养模式酷似军队(韩东育”:《东亚构造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二〇二四年第二期)。丸山真男也指出,对本职工作的自豪感更多是基于对纵向绝对价值的直属意识,而非横向的社会分工意识,这一点在日本的军队里几乎表露无遗”, 军队竭尽所有的教育方针来集中培养出此类自豪感([“日”]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八年版)。这种“自豪感”,无疑是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
比如品牌名本为“National”(国民的)的松下就在一九六二年的广告词中使用了“骄傲自豪,日本制造”,还曾在广告中结合工匠审美情趣表现了文化本质主义的技术论(《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对于争夺“世界第一”的偏执、公司对于职员成为“企业战士”“猛烈社员”甚至“公司狗”“社畜”的要求,无一不是这种价值取向的体现。在唯公司高层马首是瞻的正式工和得过且过的临时工组成的生产线上,盈利压力下的数据篡改也就成了“常识”。
斋藤正二通过分析日本国民生产生活中“修行”一词的渗透,批判了这一概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巧妙手段将‘管理’延伸到高度分工的劳动体制的所有角落”,并且培养了“勤勤恳恳和绝对服从的‘新的经济动物’”。他认为,这种日式“修行”的精神训练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强调“关注于一点”的命令,“根本不关心被命令者的工作内容是艺术还是政治,抑或是杀人”;这种教育方式导致学生丧失了将现象看作“整体”中的“部分”的“关联性把握”能力,认为不存在与眼前单一直线运动无直接关联的其他事物,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意识物象化”问题(〔日〕斋藤正二:《日本自然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正如小岛洁指出的,日本国民对于自由、独立价值的意识淡薄,“深层意义的政治”在日本是缺席的,这使得社会中难以产生强有力的变革。(〔日〕小岛洁:《建构世界史叙事的主体性》,《文化纵横》二〇一九年第三期)也正因如此,在议员、行政组织和企业及行业组织构成的铁三角内部的利益输送和制度惰性影响下,“日本制造”的相关丑闻曝光后,仍难以引发彻底的反思与变革。
“日本制造”的脆弱性在于,其指向是高效能的技术社会,而这种社会并不承认超越国境的人类普遍价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基于轻工业产品出口激增的“神武景气”,实质上是建立在朝鲜战争的军事需求之上的。甚至美军在越战期间普遍使用的非商用集装箱也曾经与军用物资一起停靠在日本,以便装载手表、电视、厨房用具等“日本制造”商品,从而加强了日美之间的贸易联系(〔美〕赖克:《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当代中国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看似单纯为了迎合一般消费者需求、与军用目的无关的“日本制造”,也拥有对其他亚洲国家命运的冷漠甚至残酷的侧面。
四、走向开放”:“日本制造”的未来可能
即便在“失去的三十年”,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与“日本制造”标签的企业仍取得了成就。如主打休闲服饰的优衣库、坚持“纯朴、简洁、环保”理念的无印良品、以“物超所值”为目标的日本最大的家居连锁店宜得利(NITORI)等。宜得利虽然创业于“日本第一”论调逐渐占据主流的七十年代,但仍将“完全模仿”(Dead”Copy)奉为信条。世嘉、索尼和任天堂等公司持续制造领先世界的电子游戏,体现出令人赞叹的创新能力。曾经将“骄傲自豪,日本制造”作为广告词的松下集团的自我定位也已经转变为“为世界文化的进步做贡献”,相应地,其品牌名称从战前的”National 更改为原本用于出口扬声器品牌的”Panasonic (“Pan”意为“全部”或“普遍”,“Sonic”意为“声音”),”寓意为“将我们创造的声音传遍全世界”。松下集团在中国家电市场历经十年低迷后,于二〇二三年扭亏为盈,并将启动重仓本地化策略”:“China”for China”“China for Global”。其二〇三〇年的愿景为“生活丰富度的维持与进步(Well-being)与地球·社会问题的解决(Sustainability)”,体现了回应全球性议题的姿态。
当前,日本经济受益于中美大国博弈的“红利”,成为美国主导的所谓盟友间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受益者,制造业工厂的回流现象日益显著(闫坤、沈建光等”:《全球化浪潮中的“日本式衰退”: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当代中国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但日本仍应勇于直面制造业领域频发的问题,重塑对制造本身的敬畏之心”;面对日元贬值和高龄少子化带来的“用工难”问题,需重审并调整劳资关系,致力于恢复和提升“劳动尊严”。
综上所述,“日本制造”应克服“日本特殊论”和“日本”VS 西欧”- 美国”图式的束缚。正如贺平指出的,日本的“异乎寻常”之处仿佛成为莫比乌斯环的搭袢,将“礼赞日本”与“指摘日本”无缝对接(贺平”:《国际日本研究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这种闭环结构无益于“日本制造”连接到更为开放的、全人类共通的普遍价值。“日本制造”的复兴应建立在打破围绕美日关系的“边境”-中心”思维图式上,反思基于此的制造业民族主义,注重与东亚近邻的共生合作。否则,曾大放异彩的“日本制造”仍可能走出散发曙光、展现辉煌、坠入暮色的轨迹。
###
来源:《日本工匠文化研究》,周菲菲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