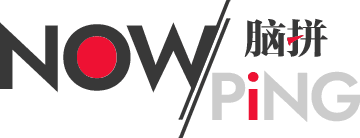《如临大敌》:真相背后的历史,可能比真相更加精彩
黄博,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与藏学的研究。著有《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等书。本文摘自《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黄博
一、1054年的谣言大恐慌
1894 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噩梦,其实甲午年的阴影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震撼过世人。宋人认为,甲午年有着奇怪的魔咒,尤其是在四川,一遇甲午必有血光之灾。五代孟知祥据蜀自立,宋初王小波揭竿而起,俱在甲午之年。当时间成为谣言的核心内容时,会更加震撼人心。民间流行的《六十甲子歌》等各种形塑大众知识与信仰的内容,构建了甲午再乱谣言得以产生的精神背景。
乱世谣言丛生,容易理解。可甲午再乱的谣言为什么会在盛世流行?宋初大乱之后,到宋仁宗初年,四川渐渐安定下来。四川的老百姓向朝廷报告,田间地头盛开着一种“太平瑞圣花”,这种花已六十年未曾绽放了。这意味着属于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已经来临。
可是开封的朝廷却不认为盛世可期,他们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四川人民节日里素来喜欢穿着古代帝王将相的“戏服”,抬着二郎神游街,却被认为是意图谋反。为了防止驻军图谋不轨,宋廷甚至禁止驻蜀军队平日里配备武器搞训练,使其成为一支不能打也不允许能打的奇葩军队。仁宗的盛世,背后暗潮涌动,于是在造反与造谣之间,宋代的老百姓选择了后者。
可惜,真出事的时候,帝王将相并不像他们自己在没事的时候自诩得那样英明神武。
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信息,皇帝其实也没有多少定力。民间更是热衷于宣扬各种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益州下属的郫县做县尉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盛传有兵变和外寇,城中富人蜂拥出逃,连金银财宝都来不及带走,只能埋在地下以待将来。各地白头翁到处吃人的谣传更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甚嚣尘上。而京城里的“帽妖”——据说是一只会飞的帽子——竟然可以来去无踪,杀人于无形,更是在天子脚下搅得满城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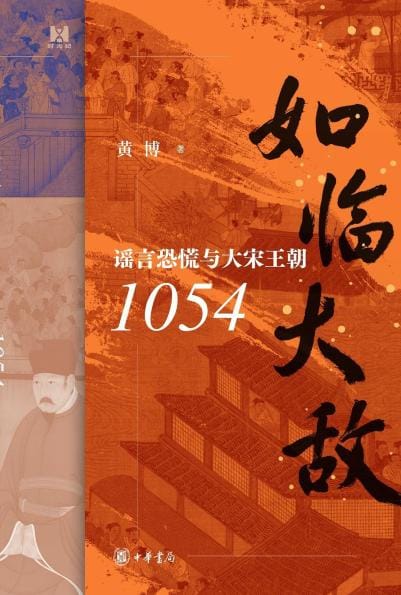
所以,当甲午再乱的谣言传来,仁宗又怎能不信!皇帝相信甲午年会有大乱,老百姓也相信甲午年会有大乱,官员们更是严阵以待。可是至和元年(1054)的甲午年却出奇的安静,“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连一场所谓的未遂的兵变,其实也只是街巷之间的妄传。当乱未乱之际,写下“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诗人张俞上书四川地方当局,直言所谓甲午必乱的传言不过是无知之辈起哄而已。他以丰富的知识与阅历,审时度势,大声疾呼“甲午之说诞矣”—甲午再乱的谣言根本就是荒诞的。谣言止于智者,读书人就应该以他们的智慧终止谣言。不过,诗人的自信心在这种时候显然有些膨胀了,现实马上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当甲午年真的来临了,那一年的天空是很可怕的。从五月起,一颗从未见过的新星出现在天关东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人们都可以看到它在天上闪耀——那是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SN1054。宋人称之为“天关客星”。占星术有言,客星临空,人间必有“兵丧饥馑,民庶流亡”。不久之后,一位失败的造反者、销声匿迹多时的侬智高突然出现在云南。民间纷纷议论,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四川,旦夕之间就会兵临城下,四川的大乱迫在眉睫。于是集体性大恐慌爆发了,老百姓被吓得“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贱卖产业,各自逃命。

该来的始终要来,大家相信甲午再乱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这时,四川官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惊慌失措,匆忙指挥老百姓做各种准备,使百姓“日夜不得休息”。官府用瞎忙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反倒让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正当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张方平来了。至于侬智高是否会来,没人知道。张方平“镇之以静”,成功地对抗了无根的谣言。他中止了一切军事准备,私下里,他也派人去打探消息,寻出谣传的源头,阻断了谣言的再生产。
新年的上元夜,成都办起了热闹的灯会,人们终于相信,这盛世一如既往。而侬智高的生死我们却无从得知。有消息说他确有袭击四川的打算,也有消息说他早就被人杀死,反正他最后不明不白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然而,甲午谣言之曲虽终,参与其事的人却未散。类似的故事在之后一千年里还有很多,百年之后,洪迈仍然相信丙午、丁未之交中国必遭大灾,而这个关于时间的谣言,从南宋中后期一直流传到近代。从皇祐四年(1052)年底到至和二年(1055)年初,甲午再乱的谣传从最初的“传闻其事”,发展到高潮时期的“諠震惊”,两年多的时间内,四川特别是成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谣言大戏。
上至皇帝下至民众,都被卷入这一既荒诞又紧张的谣言危机中。宋廷在皇祐四年十二月,即甲午年到来前夕,选择重臣程戡前往四川坐镇。从宋朝中央到四川地方当局,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最大可能让谣言不会成真。本地士人则心态复杂,他们一方面深知这是让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注意到四川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机会,但也担心谣言的疯传最后会导致局面失控,因此他们积极建言献策。张俞和苏洵就是典型代表。预期中的内乱并未发生,整个甲午年前后,既没有像一百二十年前那样出现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像六十年前那样发生人民起义,当然也没有发生宋廷一直担心的驻蜀军队的兵变,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这个时候,外来的威胁却不期而至。造反失败后不知踪迹的侬智高图谋四川的消息传来,四川社会的谣言危机被迅速放大,局势一度失控成为集体性大恐慌。最后恐慌得以平息,前后两任益州知州程戡和张方平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张方平,处理谣言危机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
在谣言危机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力量的交织,皇帝、朝廷大臣、地方官员、本地士人和民众,甚至四川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这一过程中都试图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随着事态的演进,相互交织的联系与盘根错节的纠葛一一展开。
甲午再乱谣言的兴起和变化调动了各方力量,使北宋朝廷调整了部分在四川长期施行的酷政,改善了四川的政治环境和人民生活条件。这场谣言危机的圆满解决使朝廷终于放下了长期以来对四川再度发生动乱的担忧,从此以后,四川的情形不再是宋廷的关注焦点。地方士人借此机会得以表达意见,对地方政治发挥影响。
然而,四川的民众成了谣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在谣言危机的高潮面前惊慌失措。尽管甲午再乱的谣言来自民间,是四川民众对于自己处境不满的一种宣泄,然而,在各种政治博弈中,四川民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被裹挟到这场危机的洪流之中,在甲午年下半年的大恐慌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谣言现象在古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偶然发生的谣传,常常出其不意地打乱常态下的风平浪静。在古代,社会主流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基本上都垄断在官府和知识精英手中,民间社会很难有发声并引起朝廷和地方当局注意或重视的机会。
二、从谣言看历史的虚相与实相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甚至把谣言和日食、地震、洪水、饥荒一起视为需要引起朝廷重视的国之大变。他说,“在天则有日食星变之异,在地则有震动陷裂、水泉涌溢之灾,在人则有饥馑流亡、讹言相惊之患,三者皆非常之变也”。显然,曾巩把谣言恐慌当成了一种天灾,认为其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表明上天在警告皇帝。
事实上,谣言的兴起与传播并不是天意,实际上反映了人心。它的出现以及短时间内的风靡天下,并非神秘主义逻辑下的天心难测。谣言恐慌是社会舆情最直观的反映,是民意最简单粗暴的表达,也是底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一种成本最低的手段。甲午再乱谣言的产生,是传统的宿命论、阴阳五行思想、四川地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古代另类的舆论表现形式交织而成的结果。看似偶然的甲午再乱谣言突然产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其后数年朝廷政局的发展与民间社会的运转。
因此,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人对于甲午再乱谣言的应对与利用,展示出一幅鲜活的北宋中期政治与社会的画卷。朝廷在这个过程中担心害怕而力求息事宁人;地方官员则接受了一场执政能力的考验,高良夫的惊慌失措,张方平的“以静镇之”,是这场考验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地方士绅则乘机积极参政议政,尽管张俞与苏洵在认识上截然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成都地方政府建言献策。
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由焦虑、恐惧到情绪几乎失控,从张方平抵达成都前四川民间婚姻失序、藏金埋银的惊恐举动中可以看到,无论在何种危机中,民众终究是弱势的一方。可以说,甲午再乱谣言危机成为了一个考察北宋中期王朝政治与地方社会难得的平台,它为通常只能做概论性考察的社会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入到具体运作过程中来详细观察的机会,既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小故事,又为我们展示了地方性事件的大历史。
北宋中期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不但令宋人引以为傲,也使后来元、明、清三代的文人官僚们艳羡,甚至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北宋中期,士大夫政治之所以能够稳定地运转,谣言在其中竟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澶渊之盟后,真宗的骄虚之气被激发,在战场上失掉的面子,他想要在花费巨资搞出来的大排场上找补回来。此后几年里,真宗接连搞了天书降世、泰山封禅等一系列旨在提振王朝政治正向精神的表演。他花钱如流水,引得朝野忧心忡忡,社会上关于真宗很像唐玄宗的说法开始流行。

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月的一天,龙图阁待制孙奭(962—1033)上疏提醒真宗,说他这几年做的这些事情“外议籍籍”,意思就是民间流言纷起,猜测他现在是有意在效法唐明皇(唐玄宗)。孙奭非常认真地跟真宗说,唐明皇绝对不是好皇帝,他宠爱杨贵妃,宠信杨国忠,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明皇是无道昏君。
可见,谣言就是舆情,可以成为大臣制约皇帝的舆论武器。当然,大臣们可以借机给皇帝提意见,皇帝也可以不听,比如真宗,他听了孙奭的话后不以为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疑论》,亲自下场为自己辩解。他在文章中说:“朕做的这些事情,唐明皇确实也做过。但不能因为这些事唐明皇当年做过,而唐明皇后来又搞出了安史之乱,就把他和唐朝的衰败捆绑到一起。秦始皇比唐明皇更加暴虐无道,但是现在朝廷的官僚体制、文书行政体制、郡县体制等都是秦始皇开创的。因为某人成了坏人,就把他所做的事情都看成是坏事,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真宗的这套说辞,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惜孙奭借谣言的流行上疏给皇帝提意见,最终并没有说服真宗。
仁宗与谣言的故事则要温馨得多。庆历三年(1043),曾经当过知枢密院事的大将王德用(980—1057)主政定州,把两个美女送进宫里献给仁宗。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朝堂上下议论纷纷。
这时,真宗朝著名宰相王旦(957—1017)的儿子王素(1007—1073)正在做谏官,他听说了之后,找到仁宗谈起此事,希望仁宗不要接受外臣送来的美女。仁宗好奇地问王素:“这种宫闱秘事,爱卿从何得知?”王素回答说:“臣的职责就是风闻言事。”所谓“风闻言事”,也就是可以根据谣传的消息来给皇帝提意见。在宋代,御史和谏官都有风闻言事的权力,验证传言的内容是否属实不是言官的责任,给皇帝提意见,给执政大臣找麻烦,是宋代言官的政治正确。
听了仁宗的质问,王素理直气壮地说:“陛下收了美女的事情如果是真的,陛下应该改正错误;如果没有这回事,则是谣言乱传。陛下又何必问臣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
仁宗哭笑不得,只能跟王素套近乎。他对王素说:“朕是真宗的儿子,你是王的儿子,咱们俩与别人不同,是有两代人的深厚交情在的。”
王素的父亲王旦也是一代名臣,在真宗时代当了十多年的宰相,深受真宗的尊重和信任。士大夫间的舆论对王旦的评价也比较高,王旦和真宗的关系称得上是宋代君臣关系的典范。仁宗这么说,一是缓和一下气氛,二是想让王素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放过这件事情。
但王素却不依不饶,仁宗最终只得接受了他的意见,给这两个美女各发了三百贯的遣散费,送出宫去了。此事后来被王素的儿子王巩(1048—1117)写到了他所著的小书《闻见近录》里。
在这个故事里,仁宗收了王德用献上的美女,是王素听来的八卦消息,属于“传闻其事”的流言。
真实是历史最大的生命力。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相信“眼见为实”,我们对于“看到”的历史过于偏爱。“听觉”在历史中的存在感实在太低,而谣言故事恰恰是“历史的听觉”最生动的展示。
从本书讲述的各种谣言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听说”,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庙堂之外,都是我们重建历史的主要途径。细想一下,历史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听说来的。听说得之于传闻,传闻本质上就是谣言,而谣言其实在塑造着我们所知的历史。历史的画卷绝非只是一场场文字的盛宴,它更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交响乐。在历史的乐章中,“听觉”的存在感虽然很弱,却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传统史家对于谣言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刘知几在《史通》中控诉“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谣言在历史上无处不在,传闻之事如果被写进历史往往容易使历史失真。刘知几说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谣言,比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等非常经典的故事,不但在当时会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头条新闻,在后世也会成为史家书写时的心头之好。
“曾参杀人”最早见于《战国策》。有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事情很快传扬开来。曾参的母亲正在家里织布,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曾母最初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不相信曾参杀了人,淡定地继续织布。但没过多久,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了人,曾母就有些不淡定了。等到第三个人来跟曾母说曾参杀了人,曾母终于相信了,扔下了梭子逃跑了。
“不疑盗嫂”出自《汉书·直不疑传》。西汉大臣直不疑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的重臣,官至卫尉、御史大夫,是一个忠厚宽仁的人。当时朝中传言说他和嫂嫂有苟且之事。这些谣传后来传到直不疑那里,他只是淡淡地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兄长啊!”面对谣言的中伤,直不疑的态度是懒得理会,任由谣言乱传。
“翟义不死”出自《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是西汉末年的丞相,他的儿子翟义任东郡太守,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一起起兵讨伐王莽,最后兵败被杀。翟义死后,老百姓很怀念他,都说他其实没有死。王莽篡位之后,王郎发动起义,就曾声称翟义未死,以壮声势,事见《后汉书·王昌传》。
“诸葛犹存”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习语,跟“翟义不死”一样,是因为大家怀念诸葛亮,在他死后他其实没有死。具体指的是什么事,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但语境上来看,显然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故事。
所以,刘知几说史家最讨厌“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然而,把历史上发生过的谣言摒弃在历史之外,是否就是最好的历史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谣言的出现,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击穿了厚重的正史精心编造的谎言,以夸张的方式诉说那些被遗忘或掩盖的往事。这些耳闻的碎片,或许无法像眼见的历史那样直观、明确,但它们却以独特的方式勾勒出了历史的另一面。
“听说”在历史上虽不如“看见”那般确凿无疑,却发挥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它像是历史的暗流,在表层的浪花之下涌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和人们的认知。有时,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谣言,却能在人群中激起千层巨浪,成为我们从多角度认知历史的关键因素。因此,当我们探寻历史的真实时,不应只局限于“看见”的目光,更应倾听那些“听说”的声音。它是历史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历史“听觉”的生动体现。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历史中的人物、事件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与解读的曲折过程。有助于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历史,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魅力。
传闻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给历史记录补充了各种花边新闻。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发生在基层、涉及广泛的事件,往往难以被官方记录详尽地涵盖。而传闻,正是这些事件的民间记忆,是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事实上,传闻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传闻的内容、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传闻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舆论氛围,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
当然,传闻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导性和不确定性。在享受传闻给历史叙事提供的精彩素材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审慎对待传闻,结合其他各种说法进行综合分析,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在注意到“历史的听觉”这个维度的时候,“历史的听力”也相当重要。我们能否在众声喧哗中发现历史的微妙之处?“历史的听觉”考验的是史学家的综合素养。寻找真相,但也不必执着于真相。
###
来源:學人scholar